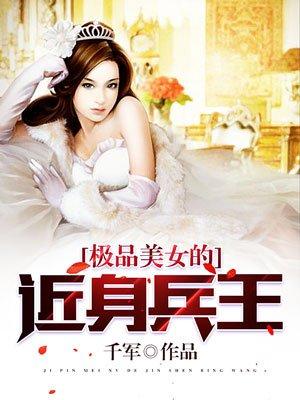趣书网>云麓词心录:白云着 > 第283章 粥香里的十年雪(第2页)
第283章 粥香里的十年雪(第2页)
煜明接过手机,照片里的红绳是子昂去年送他的,说“本命年要系红”。他忽然想起很多个这样的细节:子昂总是记得在他看书时递上温热的粥,总是在他改稿熬夜时把粥温在炉上,总是在粥里藏着他爱吃的食材,却假装“随便放的”。
“你知道吗?”煜明放下手机,声音有些发哑,“我第一次觉得不孤单,就是在你家喝的那碗腊八粥。你母亲往我碗里夹了块最大的芋头,说‘吃饱了不想家’,那时我离家三年,第一次觉得粥香里有了家的味道。”
子昂的睫毛忽然颤了颤,低头搅动着粥:“我母亲总说,你是老天爷派来给我做伴的。她走前还拉着我的手说,‘以后熬粥要给煜明多放颗枣,他胃不好’。”
炉火忽然爆出个灯花,映得两人眼眶都有些发红。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被云层遮住,只有炉火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像一幅被时光定格的画。煜明看着子昂搅动粥的手,忽然觉得这十年的光阴,都熬进了这碗粥里,每一勺都是沉甸甸的牵挂。
第三章瓷碗盛来雪后春
寅时三刻,第一缕晨光透过云层时,腊八粥终于熬好了。煜明揭开陶瓮的木盖,一股复合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红枣的甜、桂圆的醇、苏木豆的微醺,还有米粒熬化后的绵密,在晨光与炉火的交织中,像首温暖的诗。
“快来看!”子昂用瓷勺舀起一勺,粥体呈淡淡的紫,上面浮着层薄薄的油光,“这苏木豆果然把晚霞煮进去了。”他说着,小心地将粥分盛在两只蓝边瓷碗里,碗沿的冰裂纹路在粥香中若隐若现。
煜明接过瓷碗时,暖意从指尖一直熨帖到心底。他想起文档里写的“轻抿一口腊八粥,那暖便从舌尖蔓延至心房”,此刻果然如此,粥的温热带着食材的甜,像无数个被珍藏的瞬间,在口腔里一一化开。
“你放了桂花蜜?”煜明尝到一丝清冽的甜,抬头看子昂。
子昂笑而不语,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罐,罐口还沾着金黄的蜜渍:“去年秋天在岳麓山采的,一直留着等今天。你说过,桂花蜜是‘秋天藏在罐子里的甜’。”
两人捧着瓷碗坐在窗前,看雪后的纳兰园在晨光中苏醒。老梨树的枝桠上挂着冰棱,折射出七彩的光,竹梢的积雪不时坠落,惊起几只觅食的麻雀。煜明忽然想起十年前的今天,他和子昂在国子监的雪地里打雪仗,子昂把雪塞进他衣领,他追着人跑了三条街,最后在卖粥的摊子前停下,一人喝了碗滚烫的粥,额头还冒着热气。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写粥文吗?”子昂用瓷勺轻轻刮着碗边,“你负责写‘米粒在水中舒展的样子’,我写‘粥香如何爬上窗棂’,结果被主编夸‘烟火气里有诗心’。”
煜明点头,想起那篇文章里的句子:“粥沸时的气泡,是时光吐出的珍珠。”此刻看着碗里袅袅上升的热气,忽然觉得那些珍珠其实都落在了彼此的岁月里,串成了这条漫长的友情之路。
“其实我们熬的不是粥,”煜明望着窗外渐渐消融的积雪,声音很轻,“是把十年的时光、无数个清晨黄昏,都放进了这口瓮里。你看这粥里的每样食材,都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江南的苏木豆、岳麓山的桂花蜜、国子监的老红枣,还有……”他顿了顿,看着子昂,“还有你手背上的疤,我母亲留下的木勺。”
子昂的眼圈忽然红了,他别过头去,望着窗外的老梨树:“去年我病重,你说‘等你好了,我们一起熬腊八粥’,那时我就想,就算爬,也要爬到这渌水亭来。”
瓷碗在手中渐渐变凉,但心底的暖意却愈发深厚。煜明想起文档的结尾:“仿若握住了生活的真谛,静享岁月的温柔馈赠。”此刻他忽然明白,这真谛从来不是粥有多香甜,而是有个人能陪你从雪落熬到雪融,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熬成值得回味的光阴。
“明年腊八,”煜明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笑意,“我们去你母亲的坟前送碗粥吧。她肯定想知道,当年那个胃不好的少年,如今能喝下一整碗加了桂花蜜的腊八粥了。”
子昂猛地转过头,晨光落在他眼角的泪上,像落了颗晶莹的雪粒。他用力点头,喉间却发不出声音,只能举起瓷碗,与煜明的碗轻轻一碰。
“当”的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晨光里传开,惊起了枝桠上的积雪,也惊起了远处晨钟的回响。两人相视而笑,碗里的粥香与窗外的梅香交织,在这雪后的清晨,酿出了最醇厚的时光味道。
而这碗盛着十年雪的腊八粥,终将在岁月的文火里,熬成他们之间最动人的词章,等着后来人在某个相似的冬日,轻轻读起,然后会心一笑,仿佛也尝到了那从舌尖暖到心房的,名为友情的甜。
喜欢云麓词心录:白云着请大家收藏:()云麓词心录:白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