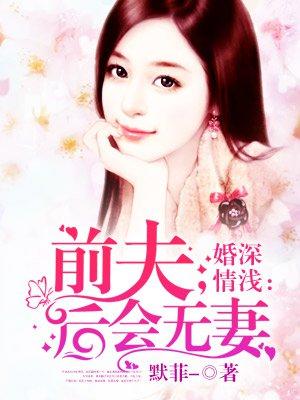趣书网>云麓词心录:白云着 > 第288章 墨痕深处是知音(第2页)
第288章 墨痕深处是知音(第2页)
煜明望向亭外的松林,那里有风声穿过琴弦般的松针:「实不相瞒,近日心中颇有些郁结,连抚琴的兴致也淡了。总觉得这世上有些情意,如同这横琴上的尘埃,看似不动,实则早已积了厚厚一层,不知从何拂起。」
景行沉默片刻,忽然从竹篓里取出一支洞箫。那箫是湘妃竹所制,竹身上斑斑泪痕,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将箫凑到唇边,轻轻一吹,一缕清越的箫声便飘了出去,与松风、泉声、鸟鸣融为一体。
箫声初时低回,如涧水潺潺,似有若无;继而转为清越,如暮云初散,林鸟归巢;最后渐渐空灵,如烟岚袅袅,直上青云。煜明听着听着,只觉心中那层积尘竟被这箫声悄然拂去,方才的「意难宁」也随之淡了。
箫声止时,景行放下箫,笑道:「琴有琴的沉郁,箫有箫的疏朗。兄若不愿抚琴,听听箫声也好。你看这烟岚,看似无依,却能寄情于天地;这涧水,看似潺潺,却能唤醒沉梦。前贤之心,未必远在千年之外,或许就在这松风泉石之间,等着我们去寻。」
煜明望着远处缥缈的烟岚,又听着脚下不息的涧水,忽然福至心灵。他取过景行手中的箫,轻轻摩挲着竹上的斑痕:「你这箫声,倒让我想起『烟岚袅袅情何寄,涧水潺潺梦自惺』这两句。或许这『情何寄』不必远寻,就在这半山亭的石案上,在你我相交的墨痕里。」
说罢,他拿起笔,在素笺上将「意难宁」改为「意初宁」,又在末尾题下「素笺淡墨写知音」七字。景行凑上前看了,抚掌笑道:「好一个『谢知音』!比『写空灵』更有深意了。你看这石案横琴,虽蒙尘未动,但若有知音在此,尘埃亦能化作琴音;这幽窗展卷,虽意初宁,然有知己相伴,墨痕亦能生出灵犀。」
此时阳光已透过亭角,在石案上投下一方明亮的光斑。景行已煮好了茶,茶汤在青瓷杯中泛起琥珀色的光,热气氤氲中,两人相对而坐,竟忘了时光流转。远处的山径上偶尔有樵夫走过,担子里的柴薪擦过路边的野菊,惊起几只蝴蝶,忽高忽低地飞进密林深处。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云麓山相遇吗?」景行忽然问道,「那时你正在溪边写生,我见你画的那株老梅,枝干如铁,却开着几簇冷艳的花,便忍不住上前搭话。」
煜明闻言失笑:「怎会不记得?你当时说我画的梅『有骨无魂』,气得我差点把画笔扔到溪里。后来还是你折了一枝真梅给我看,教我如何从梅枝的走势中见风骨,从花瓣的开合中觅魂灵。」
「可不是么,」景行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从那以后,我们便常常一起游山玩水,你写诗,我作画,倒也过得快意。只是近来俗务缠身,这样的时光竟少了许多。」
煜明端起茶杯,热气模糊了他的眉眼:「所以才要珍惜此刻。你看这半山亭,暮云来时它在这里,林鸟归时它也在这里,就像我们的情谊,不管尘世如何纷纭,总在这云麓山间,等着彼此来寻。」
一阵风过,松针落在石案上,有几片竟恰好掉在素笺上,与那墨痕相映成趣。景行拾起一片松针,在掌心揉碎,松脂的清香顿时弥漫开来:「说得是。就像你诗中说的『尘世纷纭皆过客』,但你我这样的知音,却要做这云麓山中的不老客,守着这松风泉韵,素笺淡墨,直到霜染鬓角也无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煜明望着友人含笑的眉眼,忽然觉得这半山亭的暮色也变得温柔起来。远处的烟岚不知何时已散,露出连绵的青山,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金红。他知道,所谓「心期净土」,未必在遥不可及的方外,或许就在这与知音相对的片刻,在这素笺淡墨的交辉里,在这云麓山间的每一缕风声、每一滴露水里。
第三章墨痕深处见真意
夕阳将半山亭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乎要触及亭外那片野菊。景行收拾茶具时,忽然发现石案角落有一行模糊的刻痕,像是前人留下的字迹。两人凑近细看,只见那刻痕虽浅,却风骨凛然,刻的是「会心处不必在远」六字。
「原来是谢安石的句子,」煜明轻抚刻痕,「看来这半山亭的知音之趣,早已被古人道破了。」
景行点头,将最后一件茶具放入竹篓:「古人今人,其实并无分别。你看这刻痕,历经风雨仍未磨灭,就像真正的情谊,总能在时光中留下印记。」
两人并肩下山时,夕阳已沉到山后,天际留下一片绚烂的霞彩。路过一片竹林时,晚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竟似有人在低声吟诵。煜明忽然停步,从袖中取出那两首诗笺,借着眼角余光最后的亮色,又仔细看了一遍。
「景行兄,」他忽然开口,「你说这诗中的『风吟翠竹』、『露泣黄花』,究竟是景随情变,还是情因景生?」
景行想了想,指着竹林中被夕阳染成金色的竹梢:「你看这竹子,风来则吟,本是自然之理;但在你眼中,却成了『音犹冷』,这便是情因景生,又反过来染了景物的颜色。就像我们今日在半山亭,因着彼此的相伴,连那蒙尘的横琴也仿佛有了琴声。」
煜明若有所思,将诗笺小心折好,放入袖中:「难怪古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来这情与景本就是一体的。就像你我的友情,若不是常常在这云麓山间行走,观风望云,听松看月,又怎能生出这些笔墨因缘?」
说话间已到了「听松小筑」的庭院。景行将竹篓放在石桌上,忽然笑道:「说起笔墨因缘,我倒想起一事。前日在城中见一位老画师,他说若要诗画交融,须得在『留白』处下功夫。就像你那首《感怀》,若没有『尘世纷纭皆过客』的洒脱,前面的『幽怀逸思』便显得过于沉重;而《静思雅韵》中,若没有『遥念前贤心向处』的向往,『素笺淡墨』也便失了依托。」
煜明取来灯烛点亮,暖黄的光芒顿时驱散了暮色。他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新的宣纸,忽然有了灵感:「你这话说得极是。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也要有留白的智慧。太过紧密则失了韵味,太过疏离又断了联系,唯有如这云麓山的云雾,时聚时散,方能长久。」
说罢,他提笔蘸墨,却不急于落纸,只是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景行知道他正在构思,便静立一旁,看烛影在他身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晕。庭院里的虫鸣不知何时起了,唧唧哝哝,与远处的松风遥相呼应,倒像是天地在合奏一曲夜的乐章。
忽然,煜明手腕一动,笔尖在宣纸上轻盈划过,先画了一钩残月,几点寒星,又勾出几竿修竹,数朵黄花。画面的大半却是留白,只在右下角题了两行小字:
「寒星伴月,烛影摇红,皆入君心砚;
松风横琴,露菊寄怀,尽在我笔端。」
景行凑近细看,见那画面虽简,却意境深远。尤其是那大片的留白,仿佛将云麓山的夜色、两人的情谊都融入其中,令人遐思无限。他忍不住赞叹:「妙!这留白处,正是你我友情的真意所在。看似无物,实则容纳了千言万语,胜过万语千言。」
煜明放下笔,看着自己的新作,眼中露出欣慰的笑意:「多亏了兄今日相伴,让我明白了这『留白』的道理。无论是写诗作画,还是待人处世,都不可太过满实,须得留几分余韵,容得下清风明月,也容得下知己的心意。」
此时夜已深,窗外的寒星比昨夜更加清亮,仿佛真的落进了庭院,在青石板上洒下细碎的银辉。景行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忽然回头:「明日若天晴,我们去云麓山顶看日出如何?听说那里的云海,在朝阳下宛如仙境。」
煜明点头:「好,我带上纸笔,或许能得几句好词。」
送走景行后,煜明回到书案前,见那幅「留白」的画还摊在桌上,月光透过窗棂,在宣纸上投下竹影,竟与画中的竹枝融为一体。他忽然想起景行说的「会心处不必在远」,是啊,真正的知音,不必求诸远方,就在这云麓山间,就在这素笺淡墨的交辉里,就在每一次相视一笑的默契中。
他重新拿起那两首诗笺,在「心期净土守清馨」和「素笺淡墨写知音」两句下各画了一道着重的墨痕。烛光下,那墨痕泛着温润的光泽,仿佛凝结了两人多年的情谊,也凝结了这云麓山间的风花雪月、松韵泉声。
夜深了,「听松小筑」的灯烛渐渐熄灭,只有窗外的寒星依旧明亮。在那墨痕深处,在那留白之间,知音的心意如同陈年的酒香,正在岁月中慢慢沉淀,等待着下一次的启封,等待着与清风明月、与松风泉韵,再谱一曲永恒的词心之录。而云麓山的故事,也如同这未写完的诗篇,在每一个有月的夜晚,等着知音来续,等着墨痕来书,在时光的素笺上,留下永不褪色的清馨与灵犀。
喜欢云麓词心录:白云着请大家收藏:()云麓词心录:白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