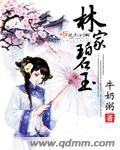趣书网>花屋湘军传奇 > 第92章 土崩瓦解(第1页)
第92章 土崩瓦解(第1页)
光绪十一年初冬,福州城被一种粘稠的湿冷裹挟着。
铅灰色的天沉沉地压在闽江口,江水浑浊,打着旋涡,卷着零星的枯枝败叶,呜咽着向东流去,仿佛也在为岸上肃穆的人群送行。
码头之上,素幡如林,在凛冽的江风中猎猎作响,出撕裂般的呜咽。
一口巨大的、覆盖着明黄缎子棺罩的楠木灵柩,被披着白色重孝的八旗兵丁缓缓地、沉重地抬上了巨大的官船跳板。
每一次脚步落下,跳板都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吱呀——吱呀——,如同垂死之人的叹息,在这片死寂中显得格外刺耳。
胡雪岩站在送葬官员队伍的最末端,离那象征着帝国最后一点刚强与远略的灵柩很远。
他身上那件玄青色贡缎夹袍早已被冰冷的雨雾浸透,沉甸甸地贴在身上,刺骨的寒意蛇一样钻进骨头缝里。
他挺直了背脊,下颌绷紧,脸上如同戴着一副精心锻造的铁面具,隔绝了所有表情。
唯有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眸子,死死钉在棺椁上那明黄的缎面,那缎面在阴霾天光下也失去了往日的耀目,黯淡得如同蒙尘的旧锦。
那里面躺着的,是他胡雪岩半生荣辱、半壁江山的基石,是左文襄公——左宗棠。
灵柩终于消失在官船深阔的舱口。一声沉闷的号炮在江面炸响,拖着长长的、凄厉的尾音。
官船沉重的铁锚在锁链的哗啦巨响中被绞起,巨大的船身缓缓移动,碾碎了江水的呜咽。
岸上,压抑了许久的呜咽和嚎啕终于爆出来,汇成一片悲声的海洋,淹没了江涛。
胡雪岩没有动,依旧钉子般钉在原地。冰冷的雨丝无声无息地飘落,渐渐连成了线,打湿了他的鬓角,顺着脸颊冰冷的线条滑下,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他紧握在袖中的双手,骨节捏得泛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点微不足道的刺痛,竟成了此刻唯一能感受到的、属于活人的知觉。
左公走了,这东南的天,彻底塌了半边。
李鸿章那张不动声色的脸,盛宣怀那双精光内敛的眼,还有那些依附于李党、早已对他阜康钱庄虎视眈眈的豺狼面孔,瞬间在他疲惫的脑海中纷至沓来。
直到官船化作江心一个模糊的黑点,彻底融入灰蒙蒙的水天交界,岸上的人群才渐渐散去,留下满地狼藉的纸钱和踩踏得泥泞不堪的地面。
胡雪岩依旧站着,像一尊被遗弃在雨中的石像。
冰冷的雨水顺着他的后颈灌进衣领,激得他浑身一颤,这才猛地从那种冰封的麻木中挣脱出来。
“老爷,”老管家胡福撑着油纸伞,不知何时已悄然立在他身后,声音嘶哑,带着无法掩饰的忧惧,“雨大了,回吧……府里,还有一摊子事等着您拿主意呢。”
胡福的话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胡雪岩强撑的硬壳。
他缓缓地、极其艰难地转过头,动作僵硬得仿佛生了锈的机括。
目光掠过胡福那张写满忧虑和岁月沟壑的脸,最终落向远处福州城黑魆魆的轮廓。
里有他庞大的阜康钱庄分号,有他囤积如山、几乎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生丝,有他苦心经营半生的商业帝国。
如今,根基已朽。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洞感攫住了他,远比这初冬的冷雨更加刺骨。
“回?”他喉咙里滚出一个干涩的音节,像是砂纸摩擦,“是该回了。”声音轻飘飘的,被风一吹就散了。
---
千里之外的天津,直隶总督行辕深处,一间暖阁隔绝了北地的严寒。
地龙烧得极旺,空气里浮动着上等银霜炭特有的、略带甜味的暖香,与窗外呼啸的北风形成两个世界。!
紫檀木大书案后,李鸿章只着一件宝蓝色宁绸夹袍,背脊挺得笔直,正专注地批阅着一份奏折。!
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边,放着一碗参汤,热气早已散尽,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
盛宣怀垂手侍立在下,姿态恭谨,目光却锐利如鹰隼,越过李鸿章的肩头,落在那份摊开的奏折上。
那正是关于左宗棠灵柩入湘、身后恤典安排的条陈。
李鸿章提笔蘸墨,笔尖悬在“追赠太傅,谥文襄”几个字上方,只略略一顿,便稳稳落下,朱砂鲜红刺目。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见半分凝滞。
“杏荪,”李鸿章搁下笔,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沉稳,如同他笔下那无懈可击的字迹,
“福州那边,该有消息了吧?”他并未抬眼,只拿起案头温热的湿手巾,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指尖上并不存在的墨渍。
盛宣怀立刻趋前半步,从袖中取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电报纸,双手奉上:“禀中堂,刚到的福州电报。
灵船已,胡雪岩在码头淋了整夜的雨,未曾登船送别。”他嘴角勾起一丝极淡、几乎看不见的弧度,像是水面掠过的一缕微风,“看样子,是真慌了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