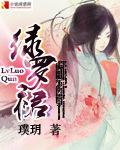趣书网>三国野史! > 第79章 曹植七步赋诗消煞 汉中王挥泪斩刘封(第3页)
第79章 曹植七步赋诗消煞 汉中王挥泪斩刘封(第3页)
诸葛亮急忙出班劝谏,羽扇轻摇,其“智谋之气”流转:“主公息怒!刘封、孟达二人固然罪无可恕,然此刻并非将其一并擒拿问罪的最佳时机。他二人久镇上庸,手握兵权,‘地头蛇之气’已成。仓促行事,逼之过急,倘若他们狗急跳墙,勾结魏贼,引兵内犯,则我益州‘安稳之局’必将动荡,正中曹丕下怀,使其‘渔翁得利之意’得逞。”
“依臣之见,”诸葛亮继续道,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不若暂且隐忍,徐图良策。主公可先行下诏,加封此二人为一方郡守,将他们分别调离上庸,使其‘兵权之意’分散,羽翼不再。如此,则如同拔了牙的老虎,再无反抗之力。届时,再寻机分别擒拿,依法处置,则可万无一失,亦能最大限度地消弭因此事可能引发的‘内乱之煞’。”
刘备沉吟半晌,强压下心中的怒火与“复仇之意”,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遂派遣使者前往上庸,名为加封,实则调任刘封为绵竹太守,令其即刻赴任。
再说那西川狂士彭羕,素来与孟达私交甚厚。他因早年出言不逊,得罪了刘备,仕途不顺,心中积郁了许多“怀才不遇之怨”。听闻刘备欲对孟达、刘封二人动手,急忙修书一封,派遣心腹之人,星夜赶往上庸,向孟达通风报信。
不料,那送信的使者刚刚出城不远,便被负责巡查的马超部下擒获。马超在益州久经沙场,其“西凉铁骑之煞”与对“背叛之意”的敏感,远非常人可比。他审问出原委,得知彭羕竟敢私通孟达,意图不轨,当即亲自前往彭羕府邸。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彭羕不知事已败露,见马超到访,还以为是同道中人,连忙热情接入,设宴款待。酒过三巡,马超故意叹息,以言语试探道:“想当年汉中王初得益州,待我等降将何等优渥,‘知遇之恩’深重。如今时移世易,汉中王似乎对我等也日渐疏远,‘信任之意’大不如前了。”
彭羕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又兼心中积怨已久,闻言不禁勃然大怒,借着酒劲破口大骂道:“那刘备老革,昏聩无能,刻薄寡恩!想我彭永年也是一代名士,‘才气’不输孔明,他竟将我投闲置散,视若无物!此等‘屈辱之怨’,我必有以报之!定要让他为此‘轻视之意’付出代价!”
马超见其上钩,又添油加醋道:“不瞒永年兄,我马孟起亦是怀此‘怨愤之意’久矣!只是苦于没有良机。”
彭羕闻言大喜,以为觅得知音,当即压低声音,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对马超密谋道:“孟起将军,你若能联络旧部,重振‘西凉铁骑之威’,再暗中结连上庸孟达为外应,我彭羕则在成都联络那些对刘备心怀不满的蜀中旧臣,以为内应。如此内外夹攻,大事可图!届时,推翻刘备伪汉,你我共享这益州‘王霸之气’,岂不快哉!”其言语中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与对刘备的切齿“恨意”。
马超故作沉吟,点头道:“永年兄此计甚妙!待我回去细细谋划一番,来日再与兄长商议具体细节。”说罢,辞别彭羕,当即带着那封密信与送信之人,星夜赶回成都,将彭羕谋反之言一五一十地禀报给汉中王刘备。
刘备听闻彭羕竟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更欲勾结孟达谋反,扰乱其“汉室正统之气”,顿时勃然大怒,厉声道:“此等反复无常、心怀‘叛逆之煞’的小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当即下令将彭羕打入天牢,严刑拷问。
彭羕在狱中受尽酷刑,方才酒醒,悔之晚矣。刘备问计于诸葛亮:“彭羕谋反之心昭然若揭,依军师之见,当如何处置,方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叛逆之煞’的影响?”
诸葛亮轻叹一声:“彭羕虽不过一介狂士,然其言语极具煽动性,所怀‘怨气’亦能感染人心。若留之日久,恐其‘叛逆之意’如同瘟疫般扩散,祸乱国家‘安定之基’。”于是,刘备下令,赐彭羕死于狱中,其家产尽数抄没,党羽亦受牵连,一时间成都城中“肃杀之气”弥漫。
彭羕被诛之事,很快便有人暗中报知孟达。孟达闻讯,大惊失色,如坐针毡,只觉一股“死亡之煞”正向自己逼近。正在他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朝廷调任刘封前往绵竹的诏书也送达上庸。孟达见刘备已然开始动手,知道自己已是危在旦夕,再无退路。他慌忙请来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仪兄弟二人商议对策。此二人乃是本地豪强,颇有“地头蛇之气”,对刘备派遣的外来官员素来阳奉阴违。
孟达面带忧色道:“二位将军,想当初我与故友法孝直一同为汉中王立下汗马功劳,助其夺取益州。如今孝直不幸早逝,汉中王竟忘了我等前功,不仅不加封赏,反而因关公之事,对我心怀‘猜忌之意’,欲加害于我。彭羕便是前车之鉴!为之奈何?”
申耽与其弟申仪对视一眼,眼中皆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申耽缓缓道:“孟将军不必忧虑。某有一计,不仅可使将军摆脱眼前危局,更能保全富贵,甚至更上一层楼,吸纳北方‘王气’以壮自身‘气运’。”
孟达大喜,急问其计。申耽压低声音道:“我兄弟二人,早有心归降实力更为雄厚的魏王曹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亦无进身之阶。将军如今正可借此机会,修书一封,痛陈刘备刻薄寡恩,不念旧情,然后毅然决然,辞别伪汉,率部归顺大魏。以将军之才,魏王必当重用。待将军在魏国站稳脚跟之后,我兄弟二人亦当率部来投,共图富贵!”其言语中充满了对曹魏“正统之气”的向往与对自身利益的盘算。
孟达闻言,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猛然醒悟。他本就对刘备心怀不满,又惧怕遭到清算,此刻听闻申耽之计,哪里还会犹豫?当即按照申耽的指点,写下一封辞别刘备的表章,言辞之间,既有对自身功劳的辩解,亦有对刘备“不公之意”的暗示,更将自己比作蒙冤受屈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充满了“悲愤之气”与“无奈之意”。他将表章交给前来催促进兵的使者,自己则连夜点起五十余骑心腹亲兵,舍弃上庸守将大印,弃城投奔曹魏而去。
前来催促孟达的使者,带着孟达那封充满“怨怼之意”的表章返回成都,向汉中王刘备奏明了孟达叛逃曹魏之事。刘备览其表章,只见其中写道:
“……臣达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功业,追桓、文之霸图,然大事草创之际,却内不能容有为之士,外不能抚功臣之心,假借吴、楚之虚名,实则‘猜忌之煞’弥漫朝堂,是以有志之士,如履薄冰,‘寒心之意’日深。臣委质以来,自问鞠躬尽瘁,然愆戾却如山之积,功劳反似水上浮萍;臣尚且自知无罪,况圣明如殿下乎?……”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臣每读古史,见申生至孝而被其父猜忌,伍子胥赤胆忠心却被吴王赐死,蒙恬为秦开疆拓土最终身负大刑,乐毅助燕连克七十余城却遭小人谗佞,未尝不扼腕叹息,泪湿青衫;不想今日臣亦亲当其事,身临其境,更觉‘天道不公之怨’,‘忠臣蒙屈之哀’,刻骨铭心!……”
“……迩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致使‘汉室气运’大损,此非战之罪,实乃‘用人不当之祸’,‘赏罚不明之愆’也!……臣卑微鄙陋,无匡扶社稷之元功,亦无擎天驾海之巨勋,自知难以见容于当今‘苛察之政’,故窃慕古代先贤之‘明哲保身之意’,早思远遁,以避‘无妄之灾’与‘身败名裂之耻’。……臣知此举有负殿下‘知遇之恩’,然‘交绝不出恶声,去臣亦无怨言’,此乃君子之风。臣资质愚钝,未能始终如一,辜负圣恩,实乃罪不容诛!愿殿下念及旧情,勉励自省,臣不胜惶恐惶恐之至!”
刘备看完表章,气得浑身发抖,将那表章狠狠掷于地上,厉声怒骂:“匹夫孟达!背叛于孤,竟还敢以这等阴阳怪气之文辞,嘲讽于我,污我‘仁德之名’!真是岂有此理!传我将令,即刻发兵,定要将此反复无常之叛贼生擒活捉,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恶气’!”
诸葛亮再次出班奏道:“主公息怒。孟达区区一叛将,不足为虑,亦不值得主公为之动雷霆之怒,损伤‘龙体之气’。为今之计,不若将计就计。主公可即刻下令,命绵竹太守刘封,领兵前往上庸,征讨叛贼孟达。此乃一箭双雕之计:若刘封能戴罪立功,击败孟达,则可将功折罪,免其一死,亦可收复上庸失地,重振我军‘声威之气’;若刘封作战不利,或是……心怀叵测,不愿与孟达死战,则其‘不忠不义之罪’更是板上钉钉,待其兵败归来,主公再将其拿下问罪,亦可杜绝悠悠众口,彰显主公‘赏罚分明之意’。如此,可一举翦除刘封、孟达这两个‘心腹之患’,何乐而不为?”
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计策,当即派遣使者,火速赶往绵竹,传下王命,令刘封即刻统领本部兵马,前往上庸,务必擒杀叛将孟达,夺回城池。
刘封接到王命,心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因关羽之事,早已在刘备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芥蒂之意”,此次出征,名为“讨贼”,实则也是一场对其“忠诚之意”的最终考验。若能成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若有差池,只怕性命难保,其魂魄亦难逃“军法之煞”的追索。他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点齐兵马,杀向上庸。
再说曹丕在邺郡与群臣议事,忽有近侍来报:“启禀魏王,蜀将孟达前来归降!”
曹丕闻言,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当即召孟达入殿。孟达入见,纳头便拜,口称“愿为陛下效死”。
曹丕故作疑虑道:“孟卿此来,莫非是效仿那蒋干盗书,行诈降之计,欲乱我大魏‘军心之气’么?”其“帝王之疑”如无形利剑,直刺孟达内心。
孟达惶恐叩首道:“臣绝无二心!皆因当初未能及时驰援关公,致使其兵败身死,汉中王刘备迁怒于臣,欲将臣处死。臣是因惧罪来降,实乃迫不得已,望陛下明察臣之‘忠心日月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