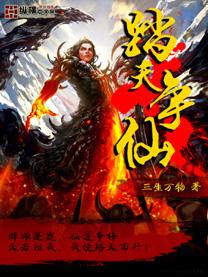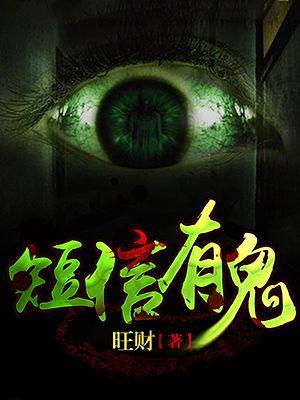趣书网>大明锦小旗 > 第二幕 粮草暗战(第7页)
第二幕 粮草暗战(第7页)
“三……三天前!”
沈砚心里一动。三天前,正是“鬼换粮”事发的前一天。这时间未免太巧了。他走到墙角,翻看那些未完工的纸人,发现其中一个的底座绑着根细麻线,线的末端打着个特殊的结——和粮仓墙角找到的麻线结一模一样。
“这结是谁教你打的?”沈砚举起麻线。
张小帅咬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最终他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是……是粮仓的刘书吏。他前几天来买纸人,看见我绑线,说我绑得松,就教了我这个结……”
刘显。又是他。沈砚想起刘显招认和张启一起拼“冤”字,现在看来,这少年恐怕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算计里。他们不仅利用了他做的纸人,还故意让他接触磁沙,好让他成为“闹鬼”的替罪羊。
“刘书吏教你打结的时候,说什么了?”沈砚追问。
“他……他问我纸人能扛多重,我说能扛半块砖。”张小帅的眼泪掉了下来,“他还说,要是纸人能扛动麻袋就好了,能帮粮仓省不少力……我当时没听懂,现在想来,他是不是早就想让纸人去扛粮?”
沈砚没回答。他看着雪地里那些歪歪扭扭的纸人,突然觉得这少年像个被线操控的纸人,自己却浑然不觉。刘显教他打结,王二郎让他搬磁沙,张启利用他的纸人制造恐慌——这孩子从头到尾,都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你别怕。”沈砚的语气缓和了些,“只要你说实话,没人会冤枉你。”他蹲下身,看着少年通红的眼睛,“刘书吏还跟你说过什么?有没有提过粮仓的粮囤?”
张小帅抽噎着,想了半天:“他……他说东墙根的粮囤‘位置不好’,让我别靠近。还说……还说要是看见有人在粮囤附近烧纸,就赶紧躲开,免得‘撞邪’……”
东墙根的粮囤,正是“鬼换粮”事发的粮囤。沈砚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精心布置的局:用磁沙拼“冤”字引王守备的旧案,用纸人制造“飘着扛粮”的假象,再让接触过磁沙的张小帅成为嫌疑人,一步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闹鬼”,掩盖他们偷粮的真相。
“王老板,”沈砚站起身,对走进来的王老头说,“这孩子我得带走问话,麻烦你照看一下他的东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王老头张了张嘴,最终还是点头:“官爷轻点待他,小帅就是个苦孩子,爹娘死得早,就靠这点手艺糊口……”
沈砚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张小帅的肩膀:“跟我走一趟吧。有些事,需要你亲眼去看看。”
少年怯生生地跟着他走出纸扎铺,手里还攥着那个没完工的纸人。雪又开始下了,细小的雪花落在纸人的眉眼上,像给那歪歪扭扭的脸添了层泪痕。沈砚回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这北境的冬天,不仅冻住了道路,还冻住了太多人的清白。但总有像张小帅手里的纸人一样,虽然粗糙,却藏着不肯被风雪压垮的韧性。
“你做的纸人,很结实。”沈砚突然说。
张小帅愣了愣,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
沈砚望着粮仓的方向,心里清楚,带这少年回去,不仅仅是为了查案。或许,这歪歪扭扭的纸人,和这慌慌张张的少年,会成为揭开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毕竟,被线操控的纸人,总有看清提线人的时候。
6。旧案重提:王守备之死
旧案尘霜
王守备的牌位摆在守备府正堂,檀香在铜炉里明明灭灭,映得牌位上的“王承宗”三个字忽明忽暗。王二郎跪在蒲团上,手里攥着半块磨损的腰牌,那是父亲生前常系在腰间的,边角被摩挲得发亮。
“我爹死前三夜,把我叫到牢里。”王二郎的声音沙哑,带着未干的泪痕,“他说那五百石粮不是丢了,是被人换了。还说粮车过秤时,有三辆明显超重,车轮都快压垮了,肯定是被人塞了沙子或石头……”
沈砚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扶手。窗外的雪又大了,风卷着雪粒打在窗纸上,像有人在用指甲轻轻刮擦。他想起苏棠昨天送来的那份旧档,是苏文记录的粮车承重明细,纸页边缘已经泛黄,上面的墨迹却依旧清晰。
“王守备提交的承重记录,你见过吗?”沈砚问。
王二郎点头,从怀里掏出张叠得整齐的纸,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份手抄的记录,字迹遒劲有力,正是王承宗的笔迹:“天启十二年冬,押运军粮一千石,行至野狼谷,三车粮承重超常规三十斤,车轴异响,疑似被调换。随行兵卒李二、赵四可证。”
“张启说这记录是‘无实证’。”沈砚看着记录末尾的批注,那是张启的笔迹,潦草而随意,“他为何不查?”
“因为他不敢查!”王二郎猛地提高声音,眼里迸出怒火,“我爹说,那三辆粮车是张启的心腹押的,过野狼谷时借口‘检修车轴’,单独停留了半个时辰!就是那时候被换的!”
沈砚沉默了。他想起粮仓里那些装着沙粒的麻袋,想起磁沙拼出的“冤”字,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如果去年的“丢粮”不是丢了,而是被换成了沙粒,那今年的“鬼换粮”,不过是故技重施。张启用同样的手法,在粮仓里演了场“冤魂索粮”的戏,既掩盖了新的贪腐,又把旧案的水搅得更浑。
“苏文的旧档里,还有别的记录吗?”沈砚问。他记得苏棠说过,她父亲的档册里,藏着不少北境粮仓的秘密。
“有。”王二郎从供桌下拖出个木箱,里面堆满了卷宗,“苏大人是个仔细人,每次粮车出入都记详单。您看这个——”他抽出一卷,指着其中一行,“天启十二年冬,张启批了‘野狼谷损耗粮五百石’,可那年冬天野狼谷根本没闹过劫匪,连雪都没下几场!”
沈砚凑近看,那行记录旁有苏文用朱笔写的小字:“存疑。王守备言车轴有异,需复核。”但复核的记录始终没有出现,只有张启的批复:“事已定论,无需复核。”
“苏大人就是因为想查这个,才被陷害的。”王二郎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找到我爹的兵卒李二,让他作证粮车被换,结果第二天李二就‘失足落河’死了,赵四吓得辞了职,跑回南方老家,再也没音讯……”
沈砚的手指在卷宗上划过,触到纸页上凹凸不平的痕迹。那是苏文反复描摹“野狼谷”三个字留下的,仿佛想从这三个字里挖出什么秘密。他突然明白苏棠为何执着于拓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被掩盖的痕迹,往往藏着最锋利的真相。
回到粮仓时,苏棠正在整理从父亲旧档里翻出的粮车图纸。她把图纸铺在地上,用石块压住四角,上面画着北境粮车的标准样式:车轴承重上限、粮袋堆叠方式、甚至连麻袋的缝针密度都有标注。
“大人看这里。”苏棠指着图纸上的车轴,“标准粮车的车轴承重是五百斤,装五十石粮刚好。王守备说的‘超重三十斤’,意味着每车多装了六斗粮——但军粮的分量是固定的,怎么会突然变重?”
“除非装的不是粮。”沈砚接口道,“是比粮重的东西,比如沙粒。”
苏棠点头:“沙粒的密度是粮食的两倍,三十斤沙粒的体积,刚好能装进半袋粮。如果把每车的半袋粮换成沙粒,既不会让粮袋显得太瘪,又能多出半袋粮,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