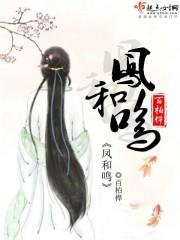趣书网>众生芸:王者浴血 > 第49章 浮云图壹(第1页)
第49章 浮云图壹(第1页)
第四十九章:浮云图(壹)
partone:青云谱上白眼羊
南昌城外。
青云谱寺的晨钟敲碎了赣江上的薄雾,余音沉闷,仿佛含着千钧重量,直直撞在朱耷的心上。他跪在佛前冰冷的蒲团上,额角抵着青砖地,僧袍宽大,裹着他嶙峋如竹的骨架,更显得空荡。
殿内光线昏昧,只有长明灯豆大的一点火苗,在佛像低垂的眼睑下跳跃,映得那悲悯的面容也忽明忽暗,捉摸不定。殿外的风,吹拂过竹林,沙沙作响,无端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朱耷,这个名字曾与天潢贵胄相连,如今,只是一件沉重的、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旧衣。他削发为僧,躲在这荒山野地,非为向佛,只为活命。
皇子?那是前世的虚妄泡影。
女神王祖贤清冷的声音,时常在他的耳边回响:“想什么想,想也有罪。”随便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血溅五步的催命符。这世道,一步踏错,便是万丈深渊。
青云谱寺这方小小的天地,青砖灰瓦,古木森森,便是他无意间寻得的、勉强能喘息的囚笼。他像五台山的鲁智深,却无那份快意恩仇的豪气,只有深入骨髓的惊惧,如跗骨之蛆,日夜啃噬。
方丈慧明年过七旬,是个枯瘦的老僧,眼神如古井深潭,仿佛能看透人心。他知晓朱耷的画技,也深知他身份的敏感与恐惧,所以初入庙门,他给朱耷的功课是每月两幅画,不多不少。
画作在月初由方丈亲自裹在青布包袱里,悄然送往山下的“墨韵斋”。那掌柜的姓李,精瘦干练,一双眼睛透着商贾的精明,却不多问一句画作来历,只按方丈的吩咐行事。
卖画所得铜钱,悉数用于寺中灯油、僧衣、米粮,维持着这方外之地清苦却安稳的运转。
日子在木鱼声、诵经声和笔墨的沙沙声中缓缓流淌。朱耷的画作上的山水、花鸟也日渐值钱,最重要的是画技也日益精进,高价求画之人趋之若鹜。
在这时,慧明方丈突然改了规矩:三月一幅,继而一年一幅。朱耷不解,一日趁着送画稿给方丈过目,终是忍不住问:“师父,弟子手勤,多画几幅,寺里用度岂不更宽裕些?”
此刻,慧明正在用一把小铜壶浇窗台上一盆半死不活的兰草,闻言停下动作,枯槁的脸上浮起一丝极淡、近乎狡黠的笑意,他捻着佛珠,慢悠悠道:
“痴儿。这世间万物,皆有其道。市井买卖,亦有其理。画作如米,多则价贱,寡则价昂。此乃‘物以稀为贵’,亦是商贾所谓的‘饥饿之法’。”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遥远的天际:“把你当成阿尔卑斯山的那只‘小山羊’,慢慢地‘薅羊毛’。你就不会跑,老衲也不必费心去追。追,是要花大力气,担大风险的。”
那“阿尔卑斯山”和“小山羊”的字眼,从方丈的口中吐出,带着一种古怪的异域腔调,显得格格不入,却又莫名地贴切。
朱耷默然。
方丈的话,剥开了这安稳表象下冰冷的现实。
他是一头被圈养、被缓慢榨取价值的羊,而青云谱寺,既是庇护所,也是无形的羊圈。这认知让他心头泛起一丝苦涩的凉意,却也奇异地减轻了那份日夜悬心的恐惧。
被利用,至少证明还有价值,有价值,便说明是安全的。他深深一揖,不再多言,心底还是感谢方丈的真诚,对自己说了那句“不中听”的实话。
但自此,他笔下的禽鸟,眼珠常翻向上,透着一股睥睨世间的冷傲与孤愤。他笔下的残山剩水,枯荷败柳,萧索荒寒,满纸尽是末世般的苍凉。
暮春时节,赣江畔草长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