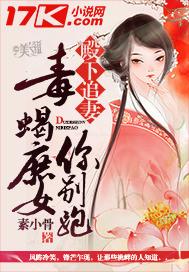趣书网>四象重启:破局者联盟 > 第146章 声波铭文 街头艺人的即兴创作被刻成城市雕塑(第1页)
第146章 声波铭文 街头艺人的即兴创作被刻成城市雕塑(第1页)
第一节:青铜上的颤音
暴雨如银线斜织,中央车站广场的青铜雕塑《共鸣》在雨幕中泛着冷硬的光。陈砚蹲在底座旁,牛仔裤裤脚早已被积水浸透,指尖划过螺旋上升的金属弧面时,触到的凹槽比记忆里更密——那些纹路细如发丝,又深似年轮,像谁用刻刀把整座城市的呼吸都凿进了青铜里。
市政档案里写着,这尊雕塑脱胎于街头艺人老周的即兴演奏。可陈砚总觉得那行字像句谎言:老周明明在五年前的冬夜冻死在地铁通道,她亲眼见过清理人员抬走他的遗体,怀里那把断了G弦的提琴还缠着半旧的蓝布条,那是他妹妹年轻时绣的。
“又来啦?”穿藏青色雨衣的保安老张举着手电筒走过来,光束扫过雕塑顶端时,雨珠顺着凹槽流淌的轨迹突然亮了亮,“这雨下得邪门,刚才我在岗亭里,听见雕塑在哼《茉莉花》,跑出来看又没声了。”
陈砚没应声,指尖停在一道歪扭的弧线上。这道纹路比周围的凹槽宽三倍,边缘还留着刻刀打滑的毛边——档案馆的资料写得清楚,林野就是握着刻刀倒在这道线上的,脑溢血发作时,他的额头正抵着青铜,像在跟雕塑说最后一句话。
雨突然变急,砸在金属上的声音混着某种低频震颤,顺着指尖爬进陈砚的骨头缝。她恍惚间听见段走调的《流浪者之歌》,琴音沙得像被砂纸磨过,尾音总带着个突兀的颤音——那是老周的标志。他拉琴时总爱用断过的G弦勉强代替,说“漏风的声音才像日子”。
“上周有个安徽来的打工仔,”老张的声音混在雨里,“摸着这道线哭了半小时,说听见他爹在讲老家麦收的事。可他爹十年前就没了。”
陈砚猛地缩回手,震颤消失了。她望着雕塑在雨里模糊的轮廓,突然想起十岁那年,母亲也是在这样的雨天牵着她的手走进中央车站,红裙下摆沾着泥点,说要去“找个能留住声音的地方”。那天之后,母亲就没再回来。
第二节:十二种震颤
市立图书馆的声学实验室里,冷气混着金属味扑面而来。李教授把十二枚传感器贴在《共鸣》的复制品上,屏幕瞬间跳出十二条起伏的波浪线,像十二条被困在玻璃里的河。
“第一节是纵向凹槽,声波频率440赫兹,刚好跟地铁3号线的报站声重合。”李教授推了推眼镜,指着最平缓的那条线,“上周三早高峰,有个孕妇说听见雕塑报‘下一站,人民广场’,可那天3号线因信号故障停运了——她男人调了监控,雕塑周围根本没人。”
陈砚的目光落在第七条线上。那线条总在雨天变得尖锐,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往上翘。“这条呢?”
“有意思了。”李教授调出一份泛黄的气象档案,1987年8月12日的台风记录上,红铅笔圈着“风速23米秒”,“林野的日记里写,他父亲就是这天没的。当时老爷子抱着台收音机躲在衣柜里,里面正放范瑞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台风把屋顶掀了时,收音机还在唱‘楼台会’。”
实验室的门被推开时,带着股潮湿的花香。穿碎花裙的周佩兰老太太攥着个铁皮饼干盒,手抖得厉害。“我是老周的妹妹。”她打开盒子,里面是张褪色的黑白照:二十岁的老周站在中央车站老站牌下,提琴盒上别着朵塑料月季,“他总说这广场的地砖缝能存声音,拉琴时特意对着地砖拉。”
李教授把传感器移到复制品的右下角。屏幕上的第七条线突然剧烈起伏,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一段模糊的越剧唱腔从扬声器里钻出来,混着哗啦啦的雨声,周佩兰的眼泪瞬间砸在照片上:“这是我嫂子生前最爱听的……她走得早,我哥拉这曲时,总说弦在哭。”
陈砚看着老太太指尖划过照片上的塑料月季,突然发现那朵花的纹路,竟和《共鸣》某道凹槽的走向一模一样。
第三节:未完成的弧线
档案馆地下室的樟脑味浓得呛人。陈砚踩着木梯翻找林野的遗物时,梯子突然晃了晃,一本蓝皮速写本从档案架上滑下来,啪地砸在积灰的地板上。
最后一页的草图上,《共鸣》的十二条凹槽末端都标着日期:1953。4。12(有轨电车通车)、1977。12。10(高考恢复)、1992。8。28(地铁1号线试运行)……唯独第十二条旁边空着,只画了个歪扭的问号,旁边用红铅笔写着“?”。
“林野去世前三天,给市长办公室发过封邮件。”管理员老王推来个铁皮柜,钥匙插进锁孔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说要在最后一节刻‘城市的呼吸声’,可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呼吸声是啥——是菜市场的吆喝?还是凌晨的垃圾车?”
陈砚打开铁皮柜最上层的抽屉,一把缠着蓝布条的刻刀躺在里面。刀刃上的青铜粉末还没褪尽,刀柄被磨得发亮,尾端刻着个极小的“野”字。她捏着刻刀掂量时,突然想起《共鸣》底座那道歪扭的弧线——长度刚好是普通凹槽的三倍,弧度像被人硬生生拽着拐了个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手机在裤袋里震动,是老张发来的视频。暴雨中的《共鸣》在发光,凹槽里渗出的淡蓝色光晕顺着纹路流淌,像无数条萤火虫汇成的河。视频最后三秒,一段清晰的女声突然冒出来,是地道的上海话:“阿林,明天带块生姜回来,你爸的关节炎又犯了。”
“这是林野的母亲,赵秀兰。”老王突然开口,手里捏着张病历单,“2003年走的,肺癌晚期。临终前总说听见天花板在唱歌,护士以为她糊涂了,其实她住的病房,窗户正对着中央车站的钟楼。”
陈砚握紧刻刀,指腹传来熟悉的震颤。这次她没躲,任由那股微弱的力量顺着手臂爬上来,像有人在轻轻拽她的袖子——就像十岁那年,母亲在车站松开她的手前,也是这样拽了拽她的袖口。
第四节:地铁里的回声
中央车站的老地铁通道正在翻新。施工队拆到第三块墙砖时,电钻突然卡住了,工人小王扒开砖缝,发现后面藏着个锈成褐色的铁皮盒,锁扣上还缠着半根小提琴弦。
陈砚赶到时,盒子已经被撬开。里面没有钱,没有信,只有盘贴着“老周的最后一曲”标签的磁带,磁带壳上用圆珠笔写着日期:2018。12。24。
“平安夜。”周佩兰老太太摸着磁带壳,声音发颤,“那天我去给他送棉袄,他说在通道里拉了首新曲子,说要刻在墙砖上。”
陈砚把磁带塞进随身听。滋滋的电流声里,先响起老周剧烈的咳嗽,像有团棉花堵在喉咙里。“今天风大,”他喘着气说,“提琴的G弦断了,就用剩下的三根拉段新的……你听,地铁进站的声音能当鼓点。”
一段陌生的旋律淌了出来。既不是《流浪者之歌》,也不是《茉莉花》,调子忽高忽低,像有人踩着碎步在雨里跑,尾音总被地铁进站的轰鸣声接走。陈砚猛地想起《共鸣》的第十条凹槽——那些斜向的纹路,和随身听屏幕上跳动的声波图谱完全重合。
她抓起包往广场跑,雨已经停了,月光把雕塑照得像块巨大的蓝水晶。指尖刚触到第十条凹槽,周围的空气突然扭曲起来,像隔着层起雾的玻璃。
她看见老周坐在地铁通道的角落,断弦的提琴斜靠在腿上,嘴里哼着刚才那段旋律。一个穿蓝白校服的女孩蹲在他对面,马尾辫上的水珠滴在速写本上,晕开一小片蓝:“周爷爷,这是写给谁的?”
“给所有等车的人。”老周笑起来,皱纹里嵌着灰,“你看那灯,一闪一闪的能当节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