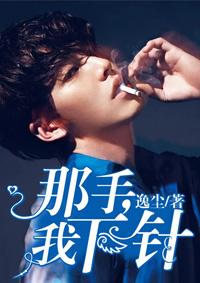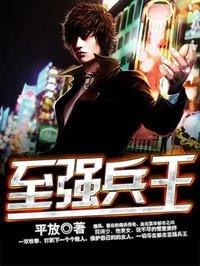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 > 第118章 技艺技术学文公十五年(第7页)
第118章 技艺技术学文公十五年(第7页)
说到子叔姬归鲁,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声音轻了些:“一个女子的去留,竟成了大国博弈的棋子。齐人送她回来,不是守礼,是炫耀——你看,我想拘就拘,想放就放。周王的命令不过是他们顺手借来的台阶,踩上去还嫌硌脚呢。”窗外的月光恰好照在“宋司马华孙”的简册上,他忽然笑了笑,“春天华耦还在为先祖的过错辞宴,秋天这‘礼’就被齐人揉成了废纸,真是讽刺。”
手指落在“齐伐曹”的记载上,他重重一点:“就因为曹文公来朝见,便要攻破人家的外城?齐懿公这哪里是伐曹,是在向天下宣告‘礼算什么’!可他偏忘了,曹国守礼,百姓心里是敬的;他恃强凌弱,诸侯表面怕,暗地里早记下了这笔账。季文子说他‘祸难不远’,怕是真的——这世上最锋利的不是戈矛,是人心的向背啊。”
风又起了,吹得书库的木门“吱呀”作响。王嘉把竹简归拢整齐,轻声道:“春夏时,‘礼’还像件打了补丁的袍子,大家好歹披在身上;到了秋冬,有人连补丁都懒得缝了,光着膀子就敢横冲直撞。可你看孟氏那两个儿子,宁死也要护住的‘礼’,曹文公冒着风险来行的‘朝礼’,不还在吗?就像这墙角的草,被风刮得贴了地,开春还是要冒绿的。”
最后那句,他说得极轻,却像一颗石子落进水里,在心里漾开一圈圈涟漪。远处的更梆敲了三下,王嘉望着案上的竹简,忽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文字里,藏着一点不肯熄灭的火星——那是乱世里,人们对“礼”最后的念想。
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过后,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夫子这话,今日才算嚼出些滋味。”王嘉指尖拂过案上一卷《论语》残简,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文字里的圣贤。他望着窗外风雪,忽然想起齐懿公破曹外城的嚣张,“齐人靠刑与力压人,百姓或许怕了,可心里的耻感早被碾碎了;曹文公守礼,哪怕国小力弱,诸侯说起他,总带着几分敬重——这‘有耻且格’,原是比城池更坚固的防线啊。”
“还有老聃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他拿起另一枚记着道家言的竹简,苦笑一声,“你看扈地会盟,晋侯嘴里的‘仁义’,不过是抢地盘的幌子;齐人送回子叔姬时说的‘恭敬’,藏着多少虚伪?这乱世的‘智慧’,倒成了钻营取巧的本事,反不如孟氏二子那句‘背离礼不如死’来得实在。”
吟诵到《墨子·兼爱》里“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时,他忽然停住,目光落在“晋郤缺入蔡”的记载上。“晋攻蔡,齐伐曹,说到底都是‘交相恶’啊。若真能‘兼爱’,何至于用连弩与戈矛说话?可墨子也说‘兼相爱,交相利’,这些诸侯偏偏只记得‘利’,忘了‘爱’。”他摩挲着竹简上“利”字的刻痕,“鲁国的连弩能百步穿杨,却挡不住齐国的侵袭;晋国的战车能踏平蔡城,却护不住盟会的体面——原来最锋利的兵器,终究填不满人心的窟窿。”
最后,他拿起记着《诗经》的简册,低声念起“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念完,长长舒了口气:“你看这天地万物,都有规矩;人心里,原是藏着向善的本性的。齐懿公再横,也挡不住季文子说他‘祸难不远’;晋侯再贪,诸侯的眼睛终究是亮的。就像这竹简上的字,刻错了能刮掉重刻,世道偏了,总有守礼的人想把它扳回来。”
风穿过书库,卷起几片碎竹屑,像是在应和他的话。王嘉将竹简一一归位,忽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文字都活了过来——孔孟的礼,老庄的道,墨翟的爱,都藏在鲁文公十五年的桩桩件件里,像暗夜里的星,虽不耀眼,却从未熄灭。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在这之后不久,转眼间便进入了师生问答环节。
王嘉将最后一卷《考工记》竹简归入“百工”类目,指尖还沾着整理时蹭到的竹屑。他摸出怀里的小竹简,上面密密麻麻刻着这几日的新疑问:“齐懿公恃力而亡,为何仍有诸侯效仿?”“晋侯弃礼逐利,却能稳坐盟主之位,礼之兴衰,究竟系于何?”字迹因反复涂改而显得有些潦草,却透着一股不弄明白不罢休的执拗。
书库外的日头已过正午,他攥着小竹简穿过回廊,远远望见左丘明先生的书房外,那株老槐树的影子斜斜铺在石阶上。先生常说“午后宜静思”,此刻窗内却隐约传来翻动简册的窸窣声,想来先生又在核对史料。王嘉放轻脚步,在门外躬身行礼:“弟子王嘉,有惑未解,敢扰先生清修。”
“进来吧。”左丘明的声音温和如常,王嘉推门而入,见先生正坐在案前,指间捏着一枚磨损的竹简,案上摊着《春秋》的注本,墨迹在阳光下泛着陈旧的光泽。
“坐。”先生示意他在对面的蒲团上落座,目光落在他紧攥的小竹简上,“看你这几日整理简册时频频蹙眉,定是有不少想法吧?”
王嘉点头,将小竹简双手奉上:“弟子观鲁文公十五年诸事,见齐懿公弃礼而用兵,晋侯假礼而谋利,却也见华耦知礼、孟氏二子守礼……弟子糊涂了,这‘礼’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
左丘明接过竹简,指尖轻轻抚过那些刻痕,忽然问:“你觉得,华耦辞宴时的谦卑,与齐懿公伐曹时的嚣张,哪一个更能让后人记住?”
“自然是华耦。”王嘉脱口而出,“齐懿公的嚣张,不过是一时之快;华耦的知礼,却被《春秋》郑重记载。”
“这便是了。”先生放下竹简,目光望向窗外的老槐树,“礼如草木,春生夏长,秋枯冬衰,看似有荣有辱,实则根脉未断。齐懿公靠力能破曹城,却挡不住身后的骂名;晋侯靠利能稳盟主之位,却掩不住诸侯的离心。你看那孟氏二子,身死却名存,为何?因他们守的不是形式上的礼,是心里的秤。”
他拿起案上的《春秋》,指着“诸侯在扈地结盟”那句:“史官不写晋侯受赂,不写齐侯无礼,只记其事,为何?不是讳言,是要让后人自己看——哪些是体面,哪些是龌龊。这便是礼的另一种模样:不在嘴上,在字里;不在一时,在万世。”
王嘉听得心头一亮,忽然想起自己刻在竹简上的“礼不可违”,原来这“不可违”,从不是指形式上的循规蹈矩,而是指人心深处对是非的坚守。他正要再问,先生却已拾起另一枚竹简:“你且看这‘晋郤缺入蔡’的记载,为何要写明‘入’而非‘灭’?”
“弟子记得,先前整理时,师哥说过,‘入’是破城而不亡其国,‘灭’是绝其祭祀,这是史官的分寸。”
“对。”先生颔首,“这分寸,便是礼。哪怕兵戈相向,也要留一分余地,这是古人的仁心。齐懿公连这分余地都不肯留,便是自绝于仁,祸难自然不远。”
窗外的风穿过槐树叶,沙沙作响,王嘉望着案上的简册,忽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文字都活了过来——华耦的辞宴是礼,史官的笔是礼,孟氏二子的死是礼,甚至晋侯受赂后史官的“不写”,也是礼的一种表达。
“弟子懂了。”王嘉起身躬身,“礼不在强弱,在人心;不在一时,在千秋。”
左丘明笑了,将小竹简还给他:“回去吧,把你的感悟也刻上去。史书如镜,照见的不仅是往事,更是未来。”
王嘉捧着竹简走出书房,午后的阳光落在身上,暖意融融。他低头看向竹简,忽然想在“礼不可违”后再加一句——“心之所向,便是礼之所存”。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他与他的那几个师哥师姐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
在此基础上,他又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感悟。
这一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接下来,到了鲁文公执政鲁国第十六个年头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