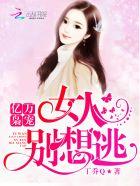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 > 第121章 文公之年尽文公十八年(第2页)
第121章 文公之年尽文公十八年(第2页)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文公第十八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文公第十八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文公第十八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文公执政第十八个年头,同时也是执政最后一年的时候,和他执政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且值得人深思的事情。
十八年春,周历二月丁丑,料峭的寒风仍卷着曲阜城头的残雪,鲁文公姬兴在宫中的台下溘然长逝。那座他曾无数次凭栏远眺的高台,此刻只剩下空荡荡的朱漆栏杆,栏杆上还留着他昨日扶过的余温。宫人发现时,案上的《周官》竹简摊开在“冢宰”篇,旁边的青铜酒樽里,残酒已结了层薄冰——这位守礼半生的国君,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多雪的冬天,十八年的执政生涯,如同一卷尚未写完的竹简,戛然停在了最凛冽的时节。
同年,西陲的秦康公罃也与世长辞。这位曾率秦军东进中原、与晋争霸的君主,其一生恰似关中平原的落日,既有过“送我者,皆自涯而返”的豪情,也难逃“崤之战”后的颓势,最终随着渭水的涛声归于沉寂,只留下“秦晋之好”与“秦晋交恶”的复杂纠葛,供列国史官笔下评说。
夏五月戊戌,齐鲁边境的麦浪正翻滚着金浪,齐国都城临淄却传来惊天变故——国人暴动,杀死了国君商人。这位以严苛着称的齐君,曾因强征民力修筑宫殿引得怨声载道,如今血溅宫廷的消息传来,曲阜城内的大夫们深夜聚议,烛火映着一张张凝重的脸:齐国的内乱,是鲁国喘息的契机,还是新一轮动荡的开端?谁也说不准。
六月癸酉,曲阜城外的汶水河畔,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鲁文公的灵柩披着玄色丝帛,在《周礼》规定的哀乐中缓缓送入预先修筑的墓陵。送葬的百姓里,有曾受惠于泗水堤坝的农夫,有在祭典上见过他庄重身影的乐师,此刻都沉默地垂首——他们或许说不清国君的功过,却记得这十八年里,曲阜的炊烟从未断过,边境的战火也鲜少烧到城门下。
秋高气爽时,鲁国的使者队伍踏上了前往齐国的路。公子遂与叔孙得臣并辔而行,车中载着给新君的贺礼,也藏着鲁国对东邻局势的试探。经过汶阳之田时,两人勒马远眺——这片曾被齐国夺走又归还的土地,如今在秋阳下泛着丰收的光泽,他们都明白,此行不仅是通好,更是要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
冬十月,寒风卷着枯叶掠过鲁国宫殿,太子恶的死讯如一声闷雷炸响。这位本应继承大统的嫡子,最终没能熬过宫廷的暗流,他的死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斩断了文公苦心维系的宗法脉络。消息传出,曲阜的学子们在泮宫前扼腕叹息,竹简上“嫡长子继承”的古训,此刻读来只剩刺骨的寒意。
同月,夫人姜氏身着素衣,登上了返回齐国的马车。车辙碾过曲阜的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位来自齐国的夫人,曾是两国联姻的纽带,如今却成了宫廷变故的旁观者,车窗外掠过的鲁国城墙,在她眼中渐渐模糊——从此,故乡是齐国,他乡也是齐国,唯有这十八年的鲁国岁月,成了夹在记忆里的残简。
季孙行父紧接着也踏上了赴齐之路。这位年轻的大夫面色凝重,行囊里装着鲁国对新君的承诺,也藏着对未来的隐忧。车轮滚滚,穿过凛冽的北风,他知道,此刻的每一步,都牵动着鲁国在列国棋局中的位置。
而南方的莒国,也在这多事之秋传来消息:国人杀死了国君庶其。这位以残暴闻名的莒君,其结局与齐君商人如出一辙。消息传到曲阜书库时,左丘明先生正提笔记录这一年的大事,笔尖悬在竹简上空良久,最终落下八个字:“乱久必治,治久必乱”,墨迹在冬日的寒气里,慢慢晕染开来。
这一年,列国的命运如走马灯般轮转,每一则简讯背后,都是城池的兴衰、百姓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春秋》里的寥寥数语,在岁月的长河里,等待着后人解读其中的沉重与无奈。
话说回来,就在鲁文公十八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匡王四年,早春时节,料峭的寒意尚未褪尽,齐国都城临淄的宫殿里,齐懿公下达了出兵伐鲁的日期。然而诏令刚发,他便突然病倒在床,面色蜡黄如枯槁,太医诊脉后摇头叹息:“君上脉象紊乱,恐难挨过今秋。”
消息传到曲阜,鲁文公闻讯,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齐懿公素来骄横,若其出兵,鲁国边境必遭涂炭,当下便命人占卜,祷祝道:“愿齐侯不及秋日便亡,以解鲁国之危。”大夫惠伯奉命将祷词告于龟甲,卜官楚丘执刀刻纹,灼烧后的龟甲裂纹却显露出诡异的纹路。他凝视良久,面色凝重地说:“齐懿公确活不到秋日,但并非死于疾病。只是我君也将听不到他的死讯了——致告龟甲的人,恐有祸患降临。”话音未落,殿内烛火忽明忽暗,众人皆觉脊背发凉。果不其然,二月丁丑这日,鲁文公在宫中猝然离世,终究没能等到齐懿公的结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说起这齐懿公,其暴戾早有根源。当年他还是公子时,曾与大夫邴歜的父亲争夺田产,最终败诉,此事成了他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及至即位,他立刻翻出旧怨,竟下令掘开邴歜父亲的坟墓,将尸体拖出,当众斩断双脚以泄愤。更令人发指的是,他非但没有处死邴歜,反而强令其为自己驾车,日日看着仇人在眼前挥鞭驭马,以此炫耀权势。此外,他见大夫阎职的妻子貌美,便强行夺入宫中,却又让阎职做自己的骖乘,与邴歜一同随侍左右,这般羞辱,简直是将二人的尊严踩在脚下。
夏五月,临淄城暑气渐盛,齐懿公带着邴歜、阎职等人前往申池避暑。池中碧波荡漾,他在亭中饮酒作乐,命二人入池洗浴。邴歜沐浴时,忽然挥起马鞭子抽打阎职,阎职怒目而视,正要发作,邴歜却冷笑一声:“人家夺走你的妻子,你都能忍气吞声,我打你一下又算得了什么?”阎职闻言,胸中怒火与屈辱交织,反唇相讥:“比起那被人斩断父亲双脚,却还要为仇人驾车的人,我这点委屈又算什么?”
一句话戳中两人痛处,相视一眼间,多年的隐忍化作同仇敌忾的杀意。他们悄悄潜回亭中,趁齐懿公醉卧之际,合力将其弑杀,随后将尸体拖入池边的竹林深处掩藏。做完这一切,两人竟从容返回城中,在宗庙祭奠过列祖列宗,才驾车逃离齐国。国中大夫们得知消息,虽震惊于弑君之罪,却也无人真心为齐懿公惋惜,最终拥立公子元即位,是为齐惠公。
此时的鲁国,正沉浸在国丧的哀戚之中。六月癸酉,鲁文公的灵柩在庄严的礼乐声中入葬,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谁也未曾想到,那位曾让鲁国寝食难安的齐懿公,已在申池的竹林中化作一具无名尸骸。两位国君的相继离世,如同投入春秋乱世的两颗石子,在列国博弈的水面上激起层层涟漪,而史书上关于这一切的记载,不过是几行简洁的文字,藏着多少惊心动魄与荒诞悲凉。
鲁文公执政的第十八个年头,亦是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春夏两季接踵而至的风波,如一幕幕跌宕的活剧,在默默见证这一切的王嘉眼前清晰铺展。那些潜藏的失落与未尽的遗憾,如细密的针脚刺透时光,让他心头发沉,不由得深深叹息。
片刻后,他抬眼望向天边流云,喉间先溢出几声沉沉的喟叹,而后缓缓开口,字句间满是沉淀后的思索:
“这半年的事,像一场急促的雷雨,来得猛,去得也烈。”王嘉望着天边渐沉的暮色,霞光正一点点被墨色吞没,他的声音里裹着未散的怅然,像被潮气浸过的棉絮,沉甸甸的,“先君十八年如履薄冰,祭天祭祖时总把‘周礼’二字挂在嘴边,可转身与晋侯盟会,又不得不低头称‘小弟’;修泗水堤坝时拍着胸脯说‘十年后必见其功’,面对公子遂的政变,却只能攥着拳头忍下——他守着周礼的体面,也藏着求生的盘算,到头来却没能亲眼看到齐国的变故,连自己身后的宗法都护不住。这‘失落’,是他拼尽全力却终究差了一步的无奈,像眼看着堤坝快筑成了,却被最后一场洪水冲垮了角。”
他抬手抹了把脸,指尖还沾着几星整理竹简时蹭上的竹屑,粗糙地划过脸颊:“齐懿公倒是活得张扬,夺邴歜父亲的田产时眼睛都不眨,掘墓斩脚时更是面不改色,抢了阎职的妻子还敢让人家当骖乘,以为强权能压得住天下,以为别人的尊严是泥捏的。最后却死在两个被他踩在脚下的人手里,死在申池的竹林里,连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这般结局,说不上解气,只觉得荒诞——可这荒诞里,又藏着多少被欺凌者的恨?像埋在土里的火种,看着灭了,遇着点风就烧起来了。”
一阵风过,书库外的老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有无数人在低声叹息。王嘉深吸一口气,胸口起伏着,像是要把这半年的憋闷都吐出来,续道:“我先前总觉得,史书上的‘功过’二字分明得很,黑是黑,白是白。可亲眼看着这些事发生才明白,先君的‘守礼’里有怯懦,‘妥协’里有担当;齐懿公的‘暴虐’里藏着自卑,‘覆灭’里也透着必然。哪是简单的对错能说清的?乱世里的人,不管是国君还是百姓,都像被风卷着的落叶,能稳住自己不坠进深沟就已不易,哪还能顾得上叶尖是朝上还是朝下?”
他低头看向手中那卷刚抄完的《鲁文公十八年纪》,竹简上的墨迹已干,透着沉静的青黑色,像凝固的时光:“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失落’与‘遗憾’好好记下。记下先君案头那盏燃到天明的灯,记下齐懿公竹林里那具无人收殓的尸身,记下邴歜挥鞭时的眼神,记下阎职忍辱时的拳头。后人翻开竹简时,能知道他们曾这样挣扎过、痛苦过、盘算过,便不算白活这一场吧。”
风又起,吹得书库门吱呀作响,卷进几片带着凉意的落叶,落在摊开的竹简上,像是在为这些未尽的话语做注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紧接着,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幻与转移…
秋意渐浓时,曲阜城外的官道上,襄仲(公子遂)与庄叔(叔孙得臣)率领的使团正踏着落叶前往齐国。此行有两层深意:一来是为齐惠公(公子元)新即位道贺,二来是答谢齐国此前派使者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车辙碾过带霜的路面,发出细碎的声响,谁也未曾料到,这趟看似寻常的出使,竟会为鲁国的命运埋下惊天伏笔。
鲁文公的后宫之中,早已暗流涌动。文公的第二个妃子敬嬴,因容貌聪慧深得宠爱,更暗中与手握重权的襄仲结下私情。她所生的儿子公子俀(即后来的宣公)年长于嫡子,敬嬴便借着这份私情,将儿子郑重托付给襄仲,恳请他助公子俀登上君位。襄仲本就野心勃勃,当即应允,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叔仲(叔仲惠伯)的坚决反对——叔仲恪守宗法礼制,力主拥立嫡子恶为君,双方在朝堂上争执不下,互不相让。
襄仲抵达齐国后,趁拜见齐惠公的机会,将立公子俀为君的打算和盘托出,恳请齐惠公出手相助。齐惠公刚登基不久,正想借着亲近鲁国稳固自身地位,又念及鲁国与齐国相邻,若能拉拢鲁国,也可制衡晋国,便爽快地答应了襄仲的请求。有了齐国这个强援,襄仲的底气愈发充足。
冬十一月,寒风卷着沙尘掠过曲阜城墙,襄仲在府邸中布下杀机。他趁着夜色,派人闯入东宫,残忍地杀死了太子恶与公子视(恶的同母弟),随后拥立公子俀为君,是为鲁宣公。对于这场违背宗法的血腥政变,《春秋》中仅以“子卒”二字一笔带过,刻意隐去了弑嫡立庶的真相,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政变次日,襄仲以新君宣公的名义召见叔仲。叔仲的家臣之长公冉务人闻讯赶来,拦在门前苦苦劝道:“大人万万不可入宫!襄仲既已弑杀二公子,此刻召您,分明是要斩草除根,入宫必是死路一条!”叔仲却挺直了脊梁,面色沉静:“若真是国君的命令,臣死而无憾。”公冉务人急得跺脚:“眼下的国君是谁扶立的?这道命令究竟是君命,还是襄仲的私意?若不是真君命,何必白白送死?”可叔仲终究拗不过心中的“忠君”执念,推开劝阻的家臣,毅然踏入了宫门。宫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再打开时,这位守礼的大夫已倒在血泊之中——襄仲命人将他杀死后,竟草草埋在了马厩的粪堆里,以此羞辱这位政敌。公冉务人见主公遇害,含泪带着叔仲的妻小逃往蔡国,直到多年后才设法为叔仲氏恢复了宗嗣,算是为这段惨烈的权斗留下一丝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