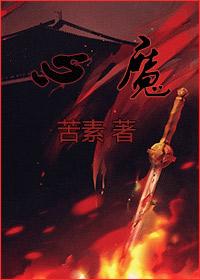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 > 第121章 文公之年尽文公十八年(第3页)
第121章 文公之年尽文公十八年(第3页)
文公的夫人姜氏(齐女)得知嫡子惨死,悲痛欲绝。她收拾行囊返回齐国时,车驾经过曲阜集市,忍不住掀开车帘,对着围观的百姓哭喊道:“天哪!襄仲无道,竟杀死嫡子,拥立庶子为君,这还有王法吗!”集市上的百姓素来敬重太子恶的仁厚,闻言无不落泪,此后便私下称姜氏为“哀姜”,以此寄托对这场冤案的痛惜。
同一时间的莒国风波,尚未平息,鲁国的动荡又牵连出更复杂的礼法争议。而远在东方的齐国,齐惠公对鲁国的“示好”并未持续太久,列国的棋局仍在权力更迭中悄然重塑。
鲁国的风波未平,宋国的内乱又起。宋武公的族人始终不满宋文公(公子鲍)的继位——毕竟文公是弑杀兄长昭公(宋昭公)上位的。他们暗中联络了昭公的儿子,打算扶持司城须(文公的同母弟)发动叛乱,夺回政权。十二月,宋文公察觉异动,抢先下手,诛杀了同母弟须与昭公的儿子,彻底斩断了叛乱的根基。随后,他命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馆舍中围攻武公的族人,将这股反对势力一网打尽,最终把武公、穆公的族人全部驱逐出境。为稳定人心,文公任命公孙师为司城,填补司城须留下的空缺;恰逢公子朝去世,又任命乐吕为司寇,通过人事调整牢牢掌控了朝政,宋国这才渐渐安定下来。
这一年的秋冬,从鲁国的弑嫡立庶到宋国的宗族清洗,列国的天空始终被权力斗争的阴霾笼罩。宗法礼制在野心家眼中形同虚设,而史书上那些简略的记载,如“襄仲杀嫡立庶”“宋杀其弟须”,背后藏着多少鲜血与哀嚎,唯有风中摇曳的旌旗与沉默的竹简知晓。
眼见在这鲁文公十八年的秋冬后两季,看着这一件件、一幕幕跌宕起伏的事件,其外在的血雨腥风与内在的权谋争斗,想必任谁的心里,都会为之触动吧。
而咱们的王嘉呢,也是在看到这一切后,内心愈发的五味杂陈,他随即在深思熟虑片刻之后,在长长叹息之余,便像先前那般,再度缓缓道出他的评价感悟与反思思考来。
“这秋冬两季的事,看得人心里像压了块冰,寒得透骨。”王嘉望着案上那卷墨迹未干的《春秋》残简,指尖在“子卒”两个字上反复摩挲,竹片的纹路硌得指腹发疼,声音里裹着书库特有的阴冷潮气,“襄仲出发去齐国时,车驾上载的是绸缎玉器,人人都说‘这是为鲁国结好邻邦’;可他从齐国回来,腰里揣的是齐侯的承诺,手里握的是杀太子的刀。谁能想到,几车礼物换来的,是东宫的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顿了顿,指尖移向另一处记载叔仲遇害的简文,声音发颤:“叔仲先生一辈子捧着‘宗法’二字,朝堂上跟襄仲争得面红耳赤,说‘嫡庶有序,如天地有常’;到头来呢?襄仲一句‘君命’就把他骗进宫,死后连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竟埋在马厩的粪堆里。那地方,连拉车的马都嫌臭啊!这礼,守得越真,死得越惨,世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王嘉拿起旁边一卷记录宋国内乱的竹简,简上“宋杀其弟须”五个字,笔锋凌厉如刀,像是能划破人的手指。“宋国更狠。同母弟啊,说杀就杀,连眼睛都不眨;先君的族人,说赶就赶,连祖宅都给烧了。先前夫子讲‘周公之礼’,说‘君臣、父子、兄弟,礼之纲也’,可现在看来,刀光比礼器管用,野心比宗法实在——谁的刀快,谁的拳头硬,谁就能说了算。”
一阵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烛火猛地一颤,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王嘉低头看向自己沾着墨痕的手,那墨痕像是洗不掉的血渍:“哀姜哭市的时候,曲阜的百姓都落泪了,有人还偷偷给太子恶设了牌位祭拜。可眼泪挡不住襄仲的刀,牌位护不住叔仲的命。叔仲先生说‘死于君命可也’,可那命根本不是君命,是襄仲的私心!我先前总信夫子说的‘史书能明善恶’,说‘笔削之间,自有褒贬’,可现在才懂,善恶明不明,全看执笔者敢不敢写——‘子卒’两个字,藏了多少刀光血影?”
他将竹简重重按在案上,竹片相撞的脆响在空旷的书库回荡,惊得梁上积尘簌簌落下:“莒太子仆杀父盗宝,季文子说‘这是凶德’,把人赶走了;可襄仲杀嫡立庶,却能借着齐侯的势坐稳权臣,还能让新君认他当恩人。同样是‘凶德’,有人被逐,有人得势——这乱世的道理,原是看谁的靠山硬,谁的算计深啊。”
“只是……”王嘉忽然放轻了声音,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竹简,落在书库最深处那排记载鲁文公事迹的简册上,那里藏着文公十八年的挣扎与坚守,“先君十八年守着的礼,叔仲先生用命护着的法,总不能就这么白废了。你看那哀姜的哭声,百姓的眼泪,还有公冉务人带着叔仲家小逃亡时,回头望曲阜城门的那一眼——那些藏在史书字缝里的东西,那些没被刀光斩断的人心,才是真的礼啊。”
烛火渐渐平稳下来,柔和的光晕笼罩着摊开的竹简,将王嘉的影子与那些竹简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像极了这乱世里,礼与权、生与死、坚守与妥协的纠缠。
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过后,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王嘉指尖悬在一卷记录叔仲遇害的竹简上空,久久没有落下。那竹片上“埋于马矢”四字,墨迹仿佛还带着未干的腥气,与周围记载礼乐的简册形成刺目的对比。他目光缓缓扫过那些浸着血与泪的记载——从太子恶的“子卒”到宋文公“杀其弟须”,从齐懿公的竹林尸骸到哀姜的集市痛哭,沉吟片刻,忽然低声吟诵起来,声音里带着穿越时空的共鸣,像是要将胸中的郁气借着先贤的字句倾泻而出。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先生这话,此刻听来竟字字扎心。”他望着窗外沉沉的暮色,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正被墨色吞没,恍惚间像是看见老子骑牛西出函谷关的背影,“先君十八年如履薄冰,祭周公时礼器摆得丝毫不差,临终前还攥着《周官》竹简,却守不住自己的嫡子;叔仲先生在朝堂上与襄仲争得面红耳赤,说‘宗法如天地纲常’,却死在马粪堆里,连只体面的棺木都没有。这世道,倒是越讲礼义,越见虚伪——襄仲在盟会上高谈‘周公之德’,转身就敢挥刀杀太子;越重宗法,越藏杀机——宋文公对着先君牌位起誓‘兄弟同心’,转头就诛了同母弟。”
转而他拿起案上一卷《春秋公羊传》,翻到“拨乱世,反诸正”的篇章,指尖在“乱臣贼子”四字上反复摩挲:“孔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眼下呢?襄仲杀了太子,还能带着齐国的盟约风光回朝,在新君面前称‘定策之勋’;宋文公弑兄逐族,反倒被史官写‘以安国人’。这‘惧’字,怕是只吓得住叔仲那样守礼的君子,吓不住襄仲、宋文公这般握刀的权臣。他们连《春秋》的笔都敢糊弄——‘子卒’二字藏了多少刀光?‘安定国人’四个字掩了多少鲜血?”
他放下公羊传,又拿起案上一卷《诗经》,手指飞快地翻到《大雅·板》篇,在“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的诗句上重重点下,竹片被按得微微发颤:“《诗》里早说‘百姓多邪僻,无法自立法度’,原来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乱世的荒唐。莒君庶其残暴,齐君商人严苛,最后都死在国人手里,倒像是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襄仲、宋文公这般‘邪僻’,却能靠着向齐国献媚、借宗族相残坐稳位子——这‘法’,究竟是约束众人的规矩,还是强者手里的工具?季文子能以‘凶德’逐莒太子,却对襄仲的弑嫡装聋作哑,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襄仲的拳头更硬罢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阵更深的寒意从脚底漫上来,王嘉猛地合上《诗经》,竹简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惊得梁上一只夜枭扑棱棱飞起。他望着书库深处摇曳的烛火,那里还摆着左丘明先生正在撰写的《左传》初稿,忽然缓缓道:“倒是《左传》里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还能让人存几分念想。齐懿公掘墓斩脚,以为能压服邴歜,终究死在申池竹林,连尸身都被野狗啃食;襄仲今日在朝堂上得意,难保日后不会被新君猜忌,不会被后人翻出旧账。或许这些佳句名篇,不是要我们看透绝望,是要我们在这礼崩乐坏的乱世里,还能认出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就像哀姜的哭声,百姓的眼泪,公冉务人带着叔仲家小逃亡时那回头一望,纵然改变不了结局,也得让后人知道,这世上曾有过不公,曾有过坚守,曾有人为了‘宗法’二字,甘愿死在马粪堆里。”
吟诵声渐渐歇止,书库重归寂静,只有案上的烛火还在微微跳动,将那些竹简上的文字照得愈发清晰。千年前的佳句与眼前的血案,先贤的叹息与今人的无奈,在摇曳的火光中交织成一片深沉的回响,久久不散。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夫子,弟子近日整理鲁文公十八年的简册,越看心里越糊涂。”王嘉捧着那册记满感悟的小竹简,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站在左丘明案前时,声音里还裹着未散的困惑,像被晨雾打湿的棉絮,“同样是弑君杀嫡,齐懿公被邴歜、阎职两个匹夫手刃,尸身抛在竹林里喂野狗;襄仲杀了太子恶与公子视,却能借着齐侯的势安坐朝堂,连新君都要敬他三分。同样是坚守宗法,叔仲先生被埋在马粪堆里,连个谥号都没留下;季文子却能捧着‘凶德’的道理驱逐莒太子,在朝堂上稳稳当当——这世道的道理,难道真的没有章法可循?”
他将小竹简轻轻摊在案上,竹片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发亮,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有对“子卒”二字的圈点,有对“襄仲杀嫡”的质疑,还有几处潦草地画着哭丧的百姓与挥刀的权臣。“弟子翻遍了《诗》《书》里的训诫,也找不到答案。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可叔仲先生的仁义,在襄仲的刀面前脆得像层窗纸,一捅就破;孔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乱臣们握着刀,连史书都敢改写——‘子卒’两个字藏了多少血?‘安定国人’四个字掩了多少罪?难道这乱世的道理,真的只剩‘拳头硬者为尊’?”
左丘明正用一方素布细细擦拭着案上那尊青铜镇纸,镇纸上刻着的“明鉴”二字已被磨得发亮。闻言他放下布巾,目光落在王嘉的批注上,苍老的指尖轻轻点过“叔仲之死”四字,那力道很轻,却像带着千钧重量:“你记不记得去年整理《晋语》,晋献公死后,里克连杀奚齐、卓子两位幼君,起初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连夷吾(晋惠公)都要让他三分;可坐稳君位后,夷吾反手就赐了他一杯毒酒,说‘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他抬眼望向王嘉,眸子里映着窗外透进的天光,清明如古镜,“权术能得一时,却不能得一世;刀光可掩一时,却掩不了万世。齐懿公的尸身烂在申池,可‘掘墓斩脚’的恶名传了列国;襄仲今日得意,可我笔下‘公子遂杀太子恶及公子视’这十个字,会跟着竹简化作灰烬吗?”
左丘明拿起案上墨迹未干的《左传》初稿,竹简上的字笔锋如刀,透着一股不容篡改的刚劲。他指着“襄仲杀嫡”的记载:“我不写‘君命’,不写‘定策’,更不写‘以安社稷’,便是要让后人一眼看清,这刀是襄仲的刀,不是天意,不是君命,是权臣的私心。至于季文子与叔仲的不同结局——”左丘明顿了顿,指尖在“守礼”二字上停留片刻,“叔仲守的是‘死谏’,他要让天下人看看,这宗法礼制还有人肯用命去护;季文子守的是‘存身’,他知道若自己也像叔仲般赴死,鲁国就再没人能挡着襄仲把周礼踩成泥了。乱世之中,守礼的方式有千万种,能让‘礼’的火种不灭,便是大功。”
王嘉望着老师笔下刚劲的字迹,忽然想起书库深处那排记载鲁文公祭典的竹简,上面详细记录着祭器的摆放、乐舞的章节,连献酒的次数都一丝不苟;又想起哀姜哭市时,百姓们偷偷抹泪的模样,想起公冉务人带着叔仲家小逃亡时,回头望曲阜城门的那一眼——那些没被刀光斩断的坚守,没被权谋磨灭的人心,不正是老师说的“不灭的火种”吗?心中那团迷雾渐渐散开,像被风吹散的晨雾,露出了底下坚实的土地。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王嘉在思虑良久之余,也是与他的那几个师哥师姐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
在此基础上,他又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感悟。
这一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接下来,到了鲁国新国君鲁宣公姬俀(倭)登基上位。同时也是其执政鲁国第—个年头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些有趣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喜欢左传游记请大家收藏:()左传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