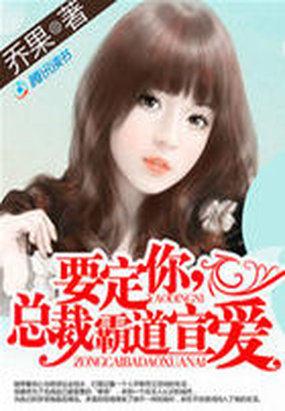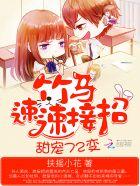趣书网>成神童后,族谱为我单开一页 > 第264章 第二道政策(第2页)
第264章 第二道政策(第2页)
淅淅沥沥的冷雨下个不停,寒风卷着湿气,无孔不入地钻进流民们那简陋的草棚。
徐飞巡视安置点时,看到不少孩童裹着单薄的破衣,缩在母亲怀里,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
他回到府衙,立刻翻开了账册。
各路商户捐赠的粮银,足够十万流民吃到来年开春。但布匹棉花,却少得可怜。
冬衣,成了新的难题。
李芳也为此愁眉不展:“国库空虚,一时半会儿也调拨不出这么多棉布。楚州的布商怕是又要故技重施。”
徐飞合上账册,神色平静:“大人,既然一招鲜能吃遍天,我们何不再用一次?”
他提笔,参照“募木策”,依葫芦画瓢,又定下了一份“募衣策”。
捐赠棉布、棉花者,同样立碑刻名,同样免除徭役,只是将“保举入县学”这一条,换成了“官府颁发‘乐善好施’牌匾,由知府大人亲自登门授予”。
对于商户而言,官府的认可,就是最好的金字招牌。
政令一下,楚州的布商们几乎没有犹豫。
有了地主们的前车之鉴,他们立刻派人将库房里的棉花布匹,源源不断地送往府衙。
短短十日,收集到的棉布棉花,堆满了府衙的三个库房。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了材料,谁来做成衣服?雇佣绣娘,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徐飞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他首接在流民安置点中,划出了一大片空地,搭建起数十个巨大的工坊。
而后,他发布了一条新的告示:凡安置点中的妇人,皆可入工坊缝制冬衣。
每缝制一件棉衣,记一工分;每缝制一床棉被,记三工分!
这些工分,同样可以在开春后兑换田地!
这条告示,彻底点燃了流民营地里那些女人们的热情。
她们的丈夫、儿子在河堤上用汗水换取工分,她们同样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为未来,挣得一份希望!
一时间,工坊里人头攒动,几乎日夜不熄。
年长的妇人,耐心地教导着年轻的姑娘如何裁剪,如何引线,如何絮棉。
一个月后,三万件厚实的棉衣,五千床温暖的棉被,被整整齐齐地分发到了每一个流民手中。
当孩子们穿上崭新的棉袄,在雪地里嬉笑打闹时;
当老人们盖着厚实的棉被,安然度过寒夜时,“徐青天”、“徐菩萨”的名号,己经在十万流民中悄然传开。
他们甚至自发地为徐飞立起了长生牌位,日夜焚香祷告。
冬衣备妥,流民心安。
徐飞终于将目光,转向农事上,
他带着几名精通农事的书吏,亲自下到田间地头,丈量勘探。
洪水退去后的土地,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
徐飞抓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尖轻嗅,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这淤泥,是天然的肥料,肥力惊人。
但坏消息是,六成以上的农田里,去岁秋播的麦种,早己腐烂在淤泥之下。
没有种子,再肥沃的土地,也只是一片荒野。
徐飞早有准备。
他修书一封,送往京城。
半月后,悬挂着“徐记粮行”旗号的船队,再次抵达楚州码头,带来了整整五千石优质的荞麦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