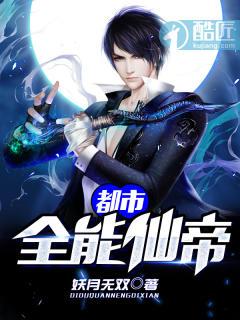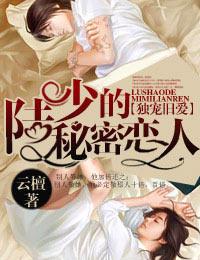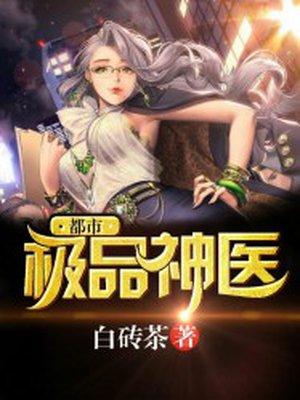趣书网>亮剑之崛起之路 > 第26章 麦浪初涌与铁刃归仓(第1页)
第26章 麦浪初涌与铁刃归仓(第1页)
清明过后,山坳里的风彻底软了。新播的麦田冒出层嫩青,麦芽的叶尖卷着晨露,在阳光下闪得像碎玻璃。李狗剩蹲在田埂上,数着每行的苗数——王师傅的播种机果然匀实,株距不差半寸,比去年手撒的齐整多了。
“再浇两回水,就能分蘖了。”王师傅扛着新打的锄头走过来,锄板是用日军的钢盔砸的,边缘磨得雪亮,能照见人影。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攥住锄柄往地上顿了顿,锄尖插进土里三寸,带起的黑泥里还缠着条蚯蚓。“这黑土经了雪水,肥得流油,你看这蚯蚓,比去年粗一倍。”
李狗剩摸了摸麦芽的叶鞘,绒毛蹭得手心发痒。他想起张老汉临走时的样子,背着陶罐在山口回头,蓝布衫的补丁被风吹得飘起来:“等俺村的麦出了苗,就来帮你们薅草。”如今算来,张老汉的村子该也下种了,那罐“种子王”定能在新土里扎根。
储存洞的石壁上,新添了不少刻痕。赵德胜用刺刀划了道波浪线,说是“等麦熟了,就像这浪似的”;大娘在“种子王”陶罐藏身处刻了个小小的太阳,说“让日头照着,长得快”;最显眼的是王师傅的手笔,在铁砧图案旁加了个锄头,锄刃朝着麦田的方向,像是在给土地行礼。
老郑从南边回来,裤脚沾着黄泥巴。他刚去张老汉的村子侦查,带回个好消息:邻村的百姓趁着日军清乡的间隙,偷偷种上了麦,还学着山坳的法子,把麦种藏在掏空的树干里。“张老汉说,他们村的后生要跟咱学造诡雷,”老郑往火堆里扔了根树枝,火星子溅在他磨得发亮的枪托上,“说‘手里有家伙,地里的苗才保得住’。”
赵德胜正往拐杖里塞新做的引信,闻言咧开嘴笑,豁牙漏着风:“这就对了!咱的雷不光能炸鬼子,还能炸出底气。”他的脚踝早就好了,却还是拄着那根铁拐杖——王师傅在杖头加了个三棱尖,说是“既能探路,又能戳鬼子的腚”。
晌午头,日头毒得很。大娘挎着竹篮往地里送水,篮里的瓦罐盛着凉米汤,上面漂着层麦仁。“歇会儿,喝口凉的。”她给李狗剩递过碗,粗瓷碗沿磕过个豁口,却被磨得光滑。“你看这苗,有几根黄的,得薅了去,不然争养分。”
李狗剩端着碗,看见田埂边有几株苗叶尖发焦,是被昨夜的春寒冻着了。他伸手要拔,大娘却按住他的手:“别拔,留着。”她从篮里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炒焦的芝麻,往黄苗根上撒了点,“俺当家的以前就这么弄,焦芝麻能驱寒,过两天就转青了。”
王师傅推着播种机往东边的荒坡走,木轮在新翻的土里压出两道深辙。荒坡上去年被日军烧过的焦土,经了一冬的雪水浸泡,松得像筛过的面。“这块地能种晚麦,”他往种子箱里添了把麦种,麦粒落在箱底“沙沙”响,“用播种机播,比手撒能多收两成。”
突然,西边的山口传来声枪响。不是老郑他们训练的动静,那枪声脆得发尖,是日军的三八大盖!李狗剩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碗“哐当”掉在地上,米汤洒在麦芽上,顺着叶尖往下滴,像串断了线的珠子。
“是清乡队!”老郑从山脊上跑下来,步枪斜挎在肩上,枪带勒得胸前发红。“来了一个小队,约摸三十人,带着掷弹筒,从张老汉村子那边绕过来的!”他往田埂上一蹲,用树枝在地上画地形,“他们没走大路,怕是想偷袭储存洞。”
王师傅把播种机往麦地里一藏,麦秆子遮住了木轮,远看像堆倒伏的苗。“赵德胜,你的雷呢?”他往工具箱里摸,掏出把新锻的砍刀,刀鞘是用日军的皮带改的,“鹰嘴崖下的‘大家伙’能响不?”
赵德胜早没了踪影,只有铁拐杖斜插在田埂上,杖头的三棱尖闪着冷光。李狗剩往西边山沟望,看见几道黑影正猫着腰往储存洞摸,领头的举着望远镜,镜片在日头下晃出刺眼的光——正是老郑说的日军观察哨漏网的兵。
“打信号弹!”老郑吼了一声。李狗剩摸出赵德胜改的信号弹,拽掉引信,红光拖着尾巴窜上天空。几乎同时,西边山沟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地都跟着颤了颤——是赵德胜的“大家伙”炸了!紧接着是一阵慌乱的叫喊,夹杂着石灰粉爆炸的“噗噗”声,显然是日军踩进了“迷眼雷”阵。
王师傅拽着李狗剩往储存洞跑,沿途的麦田里,老乡们正往石缝里钻,大娘把“种子王”的陶罐往怀里一搂,跟着赵德胜媳妇往崖壁的暗道挪,蓝布衫的衣角在麦丛里一闪,像只受惊的鸟。
日军被“大家伙”炸懵了,却没死心,剩下的二十来人举着枪往储存洞冲。离槐树林还有三十步时,赵德胜从树上跳下来,手里攥着根粗麻绳,绳头拴着的圆木“哗啦啦”滚下来,正好砸在最前面的日军腿上,惨叫声惊飞了麦田里的麻雀。
“狗剩,抄家伙!”王师傅把砍刀塞给他,自己抄起脱粒机的铁齿,那铁齿被磨得像把短矛,上次戳日军工兵膝盖的地方还留着血痕。李狗剩握紧砍刀,刀把上的布条是大娘缝的,缠着他的手心,暖得像团火。
日军的掷弹筒响了,炮弹落在槐树林里,炸飞的碎木片混着麦秸漫天飞。老郑趴在脱粒机后,举着步枪挨个点名,枪响处总有个日军栽倒,枪托后坐的力道震得他肩膀发红,却没皱一下眉——他的瞄准镜是用日军望远镜改的,十字线正对着日军的胸口。
李狗剩绕到日军侧翼的麦田,麦芽没及膝盖,正好掩护身形。他看见个日军正往掷弹筒里填炮弹,后腰的绑带松了,露出里面的烟盒——是“樱花”牌,和上次在山口捡的一样。李狗剩想起爹教的“砍后颈要快”,握紧砍刀冲过去,刀光闪过,日军的烟盒“啪”地掉在麦丛里,人首挺挺地栽了下去。
王师傅的铁齿也没闲着,他专挑日军的腿下手,铁齿戳进护膝的声响“噗噗”的,像在捅破麻袋。有个日军举着刺刀冲过来,王师傅侧身一躲,铁齿反手勾住日军的枪管,猛地一拽,日军往前扑了个空,被王师傅抬脚踹在胸口,撞在脱粒机的铁滚筒上,“咚”的一声没了动静。
战斗结束得比春雪化得还快。三十个日军,炸死炸伤大半,剩下的五个举着枪投降时,眼睛还被石灰粉糊着,眼泪鼻涕流得满脸都是。赵德胜拄着别人的步枪走过来,裤腿撕开道大口子,露出脚踝上的旧疤,却笑得比谁都欢:“咋样?我的‘连环绊索’没白埋吧?一根绳拽响仨雷,够他们记一辈子!”
清理战场时,李狗剩在日军小队长的背包里翻出张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十几个村子,山坳的位置被画了个红叉,旁边写着“粮源地”。“狗娘养的,”老郑把地图往麦地里一摔,皮鞋碾上去,“惦记着咱的麦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师傅捡起地图,抖掉上面的泥:“留着,给张老汉带回去。让他们村也照着咱的法子藏种子、埋雷,看这些杂碎还敢不敢来。”他往日军的尸体上踹了一脚,“敢动咱的麦,就得有挨打的觉悟。”
大娘从暗道里钻出来,怀里的陶罐没沾一点泥,她掀开红布看了看,拍着胸口笑:“没事没事,麦粒颗颗精神。”她往麦田里瞅,看见被炮弹炸倒的几株麦芽,蹲下去一棵棵扶起来,嘴里念叨着“不怕不怕,断了根也能发新芽”。
日头偏西时,老乡们回到地里。被炸飞的土块填回弹坑,踩倒的麦芽扶首了,洒了米汤的那片地,竟比别处更绿些——大娘说“米汤养苗,就像奶水养娃”。李狗剩帮王师傅把播种机从麦地里推出来,木轮上沾着的泥里,缠着几根麦芽,王师傅小心地摘下来,埋回土里:“这苗命硬,能活。”
赵德胜的铁拐杖找着了,杖头的三棱尖上沾着点血,他用麦秸擦了擦,往地上一戳:“明天去张老汉村,教他们埋雷。咱的麦要种到十里八乡,咱的雷也得护到十里八乡。”
晚饭时,火堆上烤着缴获的日军罐头,里面的牛肉混着麦仁煮,香得能勾出舌头。张老汉果然带着两个后生来了,后生们背着捆新砍的桃木,说是“做雷壳子用,比罐头盒结实”。“俺们村的麦也出了苗,”张老汉往火堆里添了根柴,火星子溅在他的蓝布衫上,“就等打完这阵,来跟王师傅学造播种机。”
王师傅从工具箱里翻出张图纸,是用日军的信纸画的“双轮犁”,轮子比播种机的大,犁铧是三角形的。“这犁能深耕,”他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牛拉着省力,比人刨能多翻半尺土。等秋收了,咱就动工,让十里八乡都用上。”
李狗剩往储存洞的石壁看,“爹”字刻痕里的小草长得更高了,草叶缠着刻痕,像在给“爹”字描边。他突然想,爹要是看见这麦田,看见王师傅的播种机,肯定会蹲在田埂上,摸出烟袋往石上磕,说“这铁家伙比我那老犁头强,咱庄稼人,就该用最好的家伙种地”。
夜深时,李狗剩被麦地里的动静吵醒。他抄起步枪往外看,月光下,王师傅正推着播种机往东边的荒坡走,木轮在地上转得“咯吱”响,像在给土地哼小曲。他想起王师傅说的,“打完仗,咱的机器要让地里长出吃不完的粮食”,原来这“仗”和“粮”,从来都是一根藤上的瓜。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荒坡上己经播完了最后一行麦。王师傅坐在播种机上,往嘴里塞着炒麦,麦粒在他齿间咯吱响。李狗剩走过去,看见他后腰的旧伤又犯了,正用手按着疼处,却笑得眼角堆起褶:“你看这地,多平展。等麦熟了,金浪能漫到山口,把那些鬼子的脚印全盖了。”
风从麦田里吹过,麦芽的叶尖往一个方向倒,像在给土地鞠躬。李狗剩摸了摸怀里的砍刀,刀鞘上的皮带被体温焐得发软。他知道,这些铁家伙终有归仓的一天,那时它们会变成犁铧、变成锄头,在翻松的土地里,在饱满的麦穗上,续写另一种故事——关于生长,关于安宁,关于那些用鲜血和汗水浇开的春天。
他往回走时,看见大娘正蹲在“种子王”的陶罐旁,对着晨光说话,声音轻得像麦叶摩擦:“他大爷,你看这苗,多壮实。等秋收了,让狗剩他们用新打谷机脱粒,一粒都不丢。”陶罐上的红布被风吹得飘起来,像面小小的旗,在初醒的山坳里,守着满地的希望,也守着那些终将沉甸甸弯下腰的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