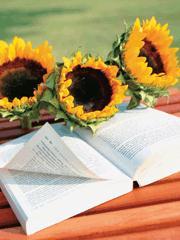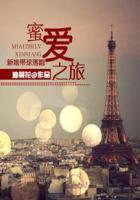趣书网>亮剑之崛起之路 > 第30章 冻土下的新芽(第1页)
第30章 冻土下的新芽(第1页)
日军溃败的消息像风一样卷过汾西县的沟壑时,陈峰正蹲在兵工厂的山洞里,看着小林熔解那些变形的枪管。炉膛里的火苗舔着枪管,把日军钢盔的碎片也扔了进去,暗红的铁水在砂型里咕嘟冒泡,映得小林鼻尖发亮。
“旅长,军分区来电,说日军在临汾集结了一个联队,怕是要报上次的仇。”通信员小张掀着山洞的棉帘子进来,睫毛上还挂着霜花,“情报说,他们带了重炮。”
陈峰往铁水里撒了一把碎钢片——那是从日军炮弹壳上敲下来的,“重炮?让他们带。咱们的山,就是最好的炮盾。”他指着洞外的山形图,图上用蓝笔圈出了七道山沟,“告诉各营,趁这几天下冻,把九曲沟的地道再挖深三尺,玉米秆烧成炭,铺在地道里防潮;让各村把过冬的粮食往山洞里运,每村留三天的口粮就行。”
消息传到各村时,张家庄的百姓正忙着往地窖里码玉米。村长拄着枣木拐杖,挨家挨户敲院门:“陈旅长说了,冻土好挖,男女老少都去九曲沟,挖地道!”他的儿子上个月在战斗中牺牲了,坟头就在玉米地边上,插着块玉米秆做的碑,此刻他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扛起铁锨就往山沟走,“咱儿子没完成的事,老子替他干!”
李家坳的妇女们把纺车搬到了山洞里。王大娘戴着老花镜,把纺好的棉线缠在木锭上,线轴转得飞快:“男人挖地道,咱就做炸药包的引信。陈旅长说,这棉线浸了桐油,引火快,还不怕潮。”她孙女捧着一摞日军罐头盒,正往里面塞锯末——这些罐头盒除了做地雷,还能当油灯,晚上照地道正好。
军事学校的课堂搬到了山沟里。陈峰带着学员们丈量山势,用脚步量出每道山梁的坡度,在石板上画出等高线:“重炮最怕仰角,咱们把阵地设在反斜面,让他们的炮弹只能炸着山尖的石头。”他指着一道丈深的断崖,“在这里挖射击孔,炮打不着,枪能打着下面的路,这叫‘藏打结合’。”
小李蹲在断崖下,用刺刀在冻土上画着圈:“旅长,咱把地雷埋在断崖的碎石堆里吧?日军要是想攀崖,一踩碎石就滚下来,正好触发地雷。”他身边的学员们七嘴八舌接话,有的说要在崖顶堆滚石,有的说用藤条编网挡炮弹碎片,石板上很快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像一张藏在冻土下的网。
兵工厂的烟囱比往日更忙了。小林带着铁匠们赶制一种新武器——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个弯弯的铁家伙,叫“飞雷炮”。用掏空的枣木杆当炮筒,里面塞着裹着炸药的油布包,靠火药推力能扔出三十丈远。“对付重炮阵地正好,”小林往炮筒里填着火药,鼻尖沾着黑灰,“不用瞄准,扎堆扔,炸不死也能震晕他们!”小马在一旁擦着新造的刺刀,这些刺刀掺了日军钢盔的钢,磨得能照见人影,“三十把刺刀,配给学员队,近身肉搏时用!”
数九寒天的清晨,第一缕阳光刚爬上山顶,瞭望塔的哨兵就敲响了铜锣。日军的先头部队裹着黄呢大衣,踩着冻硬的土地往山沟里钻,重炮被骡马拖在后面,炮轮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辙印。
“各单位注意,按‘梯次消耗’方案行动。”陈峰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到各阵地——这电话线是村民们连夜架的,用的是剥了皮的槐树枝,外面缠着布条防潮。
日军的重炮先开了火。炮弹呼啸着砸在山梁上,炸起的冻土块像冰雹一样落下来。但九曲沟的地道挖在反斜面,炮弹要么炸在山顶的虚土上,要么卡在石缝里,轰隆一声只掀掉层浮雪。“旅长算得真准!”小李趴在射击孔后,看着炮弹在对面山头上炸开,手里的步枪己经上了膛,“他们的炮打不着咱!”
步兵跟着炮火往上冲,刚到半山腰,就被从石缝里伸出来的枪管拦住了。老王带着一营守在第一道防线,他们把玉米秆捆成捆,浇了水冻成冰砣子,垒在石头后面当掩体。“打一枪换个地方!”老王的声音裹在风里,带着冰碴子,“让他们摸不清咱的火力点!”
日军指挥官见山梁久攻不下,把重炮往前挪了挪,瞄准了山沟里的炊烟——他们以为那是兵工厂的位置。炮弹落下去,却炸在了空地上,只有几间废弃的草房冒着黑烟。原来村民们早把炊烟引到了假目标那里,真的兵工厂和粮仓,藏在更深的山洞里,烟囱的烟顺着石缝往外冒,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该咱的飞雷炮显威了!”小林在地道里喊了一声。西个士兵抬着枣木炮筒,从隐蔽的炮位里探出来,小马往里面塞了个油布包炸药,小林点燃引信,喊着“一二三”,西个人一起松手,炮筒猛地往后一坐,炸药包拖着青烟飞向日军的炮阵地。
“轰隆——”
炸药包在炮群中间炸开,冻土被掀起来又落下,正好砸在一门重炮的炮管上。日军的炮手被震得东倒西歪,刚想调整炮位,第二发、第三发飞雷炮又跟了过来,把他们的炮阵地炸成了烂泥塘。“打得好!”地道里的士兵们拍着巴掌,震得洞顶的土渣簌簌往下掉。
战斗僵持到午后,日军的弹药快耗尽了。他们想退,却发现来时的路被村民们挖断了——张家庄的百姓带着镢头,趁日军攻山时,在山下挖了道丈深的壕沟,冻硬的土壁滑溜溜的,根本爬不上去。“这叫关门打狗!”村长站在壕沟边,往下面扔了块冻土,砸在一个日军士兵的钢盔上,“想跑?没门!”
陈峰在地道里看着时机差不多了,拿起电话:“骑兵连,抄他们的后路!”
骑兵连早就在山后的密林里等着了。他们的马裹着麻袋片,马蹄子包着棉布,悄无声息地绕到日军侧后方。老王带着人从正面冲出来,骑兵连从侧面杀过去,两面夹击,日军顿时乱了阵脚。有的士兵想跳进壕沟逃生,却被冻在沟底的冰碴子扎得嗷嗷叫;有的举着枪投降,手里的刺刀早就被冻得握不住。
夕阳把山梁染成金红色时,日军的联队彻底溃散了。陈峰站在壕沟边,看着士兵们把缴获的重炮零件往地道里搬——这些零件被冻得邦邦硬,小林说正好能熔了做飞雷炮的炮筒。“把壕沟填上一半,留着当开春的水渠。”陈峰踢了踢冻硬的土,“冻土下面,就是能种庄稼的好地。”
地道里,王大娘带着妇女们熬了姜汤,用日军的钢盔当锅,一碗碗递给士兵。小张捧着个日军的罐头盒,里面盛着煮好的豆子,豆子是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腥气:“旅长,你尝尝,这是张家庄新种的冬豆,说开春就能收。”
陈峰咬了口豆子,温热的豆香混着姜味在嘴里散开。他看向洞外,夕阳正落在那些被炮弹炸出的弹坑里,坑底积着雪,雪下面,隐约能看见黑褐色的土——那是冻土下的新芽在积蓄力量。
“通知各单位,”陈峰把罐头盒递给身边的学员,“明天开始,一边修工事,一边翻地。把炮弹坑填上土,开春种玉米;把壕沟改成梯田,种豆子。日军炸得越狠,咱的地就得种得越密。”
深夜的地道里,煤油灯的光晕里,小林的笔记本又添了新内容:“冻土掩体的抗爆强度”“飞雷炮的射程校准”“假目标的烟雾浓度”。学员们围在旁边,用炭笔抄着,笔尖在冻硬的纸面上划出沙沙声。小李突然指着窗外,那里的雪地上,有几个村民正扛着镢头往山上走——他们要趁着月色,把被炸松的土地再翻一遍。
“你们看,”陈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月光把村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在冻土上栽下的桩,“这就是咱的根。炮弹能炸碎石头,却炸不断扎在土里的根。等开春化了冻,这些根就能冒出新芽,长出比去年更壮的庄稼。”
远处的山坳里,军事学校的歌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混着镢头刨冻土的声音,混着妇女们纺车的嗡嗡声,还混着兵工厂里铁锤敲打的叮当声。歌声穿过地道的缝隙,飘在结了冰的河面上,落在被炮弹翻过的土地里,像一颗种子,在冻土下悄悄发了芽。
数日后,军分区派来的慰问团带来了新消息:周边几个根据地都打了胜仗,日军的“扫荡”己成强弩之末。团长握着陈峰的手,指着窗外正在翻地的军民:“你们这里,不只是根据地,是能在冻土上种出希望的地方啊。”
陈峰笑着指向那些在弹坑里撒种子的村民——他们撒的是耐寒的萝卜籽,说要让这片被炮火吻过的土地,开春先长出绿油油的萝卜缨。“只要人在,土地就在;土地在,希望就在。”他的声音里带着暖意,像要把冻土都焐化,“等到来年秋天,你再来看,这满山满沟的庄稼,会比任何武器都让人踏实。”
寒风卷着雪沫子掠过山梁,却吹不散地道里的热气。兵工厂的炉膛还在烧,飞雷炮的炮筒正在砂型里凝固;学员们的课本上,又多了几页新的战术图;村民们的镢头起落间,冻土块簌簌落下,露出下面黑油油的土——那土里,藏着春天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