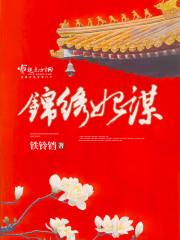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直播一战,法国人先傻了! > 第100章 被英法独吞的胜利果实(第2页)
第100章 被英法独吞的胜利果实(第2页)
“看啊!那个天真的美国佬!”
伦敦的酒吧里,巴黎的咖啡馆里,甚至柏林的街头(一些暂时忘记战败之痛的德国民众),几乎同时爆发出阵阵毫不掩饰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哄笑。
“十西点?新世界秩序?”一个伦敦绅士摇晃着酒杯,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轻蔑,“我们的威尔逊总统,是还没睡醒吗?他以为欧洲是他们的西部荒野?靠一纸空文就能驯服?”
“国际联盟?英法的工具?说得太对了!”
一个巴黎的老议员叼着烟斗,对同伴笑道,
“美国人?他们懂什么欧洲?打了一仗,死了些人,就以为能当世界警察了?结果呢?被我们和英国绅士们联手请下牌桌了!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混到!哈哈哈!”
“新孤立主义?滚回美洲?”另一个声音嘲弄道,“早该如此!欧洲的事情,从来都是英法说了算!那个暴发户,还是回他的农场玩泥巴去吧!”
1914年6月27日的欧洲人,尚未经历战争的残酷,更未体会到美国工业怪兽在战争后期展现的恐怖力量。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傲慢里,美国,即使顶着“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名头,也不过是个粗鄙、天真、缺乏政治智慧的“乡巴佬”。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撞上英法老牌列强的现实政治,撞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成了整个欧洲上流社会茶余饭后最大的笑柄。
这刺耳的、来自欧洲的嘲笑声,如同无数根钢针,狠狠扎进了每一个身处欧洲的美国人心头。
美国驻柏林大使馆。
大使脸色铁青,将一份刚刚收到的国内训令狠狠摔在桌上。文件散落一地。
“耻辱!奇耻大辱!”他低声咆哮,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十一万条美国小伙子的命!换来了什么?换来了英法的背信弃义!换来了我们被当傻子一样耍!连国联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威尔逊…威尔逊这个…”
后面的话,他终究没能骂出口,但通红的眼睛和紧握的拳头说明了一切。
巴黎的学术沙龙。一位知名的美国学者,本在侃侃而谈美国对欧洲文明的贡献,此刻却像被掐住了脖子,脸涨得通红。
听着周围法国学者们毫不掩饰的、对威尔逊和美国“天真”的讥讽,他猛地站起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那份被背叛、被轻视的怒火,灼烧着他的理智。
伦敦的证券交易所。
几个美国商人聚在一起,脸色阴沉地看着天幕,听着周围英国人幸灾乐祸的议论(夹杂着对法国要天并鲁尔的妒忌和对美国吃瘪的快意)。
“狗屎!”一个年轻商人忍不住低声咒骂,“我们投了那么多钱!支持协约国!结果呢?英法吃饱了,转头就把我们踢开!连口汤都不给!这生意做得真他妈憋屈!”他烦躁地撕碎了手中一张原本可能签订的合同草稿。
慕尼黑街头。那个屡次报考艺术学院失败的落榜生——阿道夫,正蜷缩在破旧的椅子上。
他原本麻木的眼神,在听到天幕讲述美国被排挤、英法独霸时,闪过一丝病态的兴奋和扭曲的快意。
看吧!这就是英法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一样的卑鄙无耻!
德意志被他们踩在脚下,连自以为是的美国佬也被他们当猴耍!
他干裂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仿佛在咀嚼着这份“世界不公”的苦涩滋味,将其转化为内心深处更黑暗的养料。
而在巴黎左岸的一间公寓窗台前,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猛地合上了他的笔记本。
他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
天幕上美国被戏耍的画面,欧洲人刺耳的嘲笑,同胞们愤怒而无助的表情…像烈酒一样在他血管里燃烧。
他抓起笔,不是记录,而是宣泄!笔尖狠狠戳在粗糙的稿纸上,发出沙沙的、带着杀气的声响。
标题力透纸背:《永别了,武器》!
他要写!他要告诉所有美国人,大洋彼岸那场该死的战争,从头到尾,都跟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美国人流的血,是愚蠢!是背叛的代价!他们根本就不该踏足那片被诅咒的、充斥着欧洲佬虚伪与贪婪的土地!
稿纸上,未干墨迹的标题,像一道决绝的伤口,也像一声悲愤的呐喊。被英法独吞的胜利果实,其苦涩的滋味,正化为无形的怒火,在大西洋两岸悄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