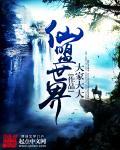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 > 第382章 为陆瑛赐婚(第1页)
第382章 为陆瑛赐婚(第1页)
史澜点点头,声音低缓:“刑部尚书许茂,你应还记得。”
“当然记得。”史芸不假思索地接道,“许家在北地那头的根基深厚,许茂为人干练果断,是朝中少有的清正之臣。他那长子许敬德,听说三年前中过进士,如今在大理寺挂名,也极有前程。”
“不过他年纪比陆瑛大些。”
“年纪相差三岁。”史澜点头,“倒不碍事。许敬德这个人,我细细打听过,行事谨慎,为人沉稳,最要紧的是,没旁门左道的习气。”
“我跟你娘看过他们的八字,虽不信这些,但也图个吉利。果然相合。”
史芸没急着接话,而是端着茶盏在指间转了转,轻声道:“爹的意思,是让我出面,为陆瑛赐婚?”
史澜直言不讳:“这事儿,若是咱史家单方面去提,许家未必就应得这般干脆。可你若以贤妃之位出面,替表妹赐婚,甚至以宫中首倡通婚之名册立,那就是圣眷所及。”
“这不光是陆家攀了高枝,也是许家得了脸面。”
“他们俩若成,这桩亲事就成了宫中主导南北通婚的第一宗,谁还能说咱这事只图声势?”
“到那时候,再推第二家、第三家……世人便不会再观望。”
史芸听着,心中已有几分明了。
她没立刻应下,而是缓声道:“爹,赐婚之事非同儿戏,不是我一句话就能拍板的。”
“但我知道你这一步,是想借宫中之势,替这件事打个样。”
“赵桓若知晓这桩婚事背后意味,只怕比我还要乐意促成。”
她站起身来,缓缓踱了几步,才轻声道:“这件事……我会安排。”
“你这孩子,果然不是只会把后宅打理得稳的。”
史芸笑了笑:“赵桓说了,眼下咱们做的每一步都不是家事,是国事。”
“既是国事,那便要走得有章有法,落得每一步都稳。”
她望向窗外,语气轻缓,却字字有据:“陆瑛是我的表妹,我不许她走得委屈;这天下是赵桓在扛,我不许他走得孤单。”
“既然是走在前面的人,就要稳得起天下的风声。”
厅中一时间静默下来,火炉中噼啪轻响。
史澜端起茶盏,望着女儿点了点头,神情里是难得的欣慰与一丝……轻松。
“你啊,果真长大了。”
史芸笑意未褪,慢慢在座中坐下,手指轻抚茶盏边沿,似是回味,又像在权衡。她沉默了一瞬,随后抬眼看向父亲,语气温缓,却不失分量地道:
“姨父陆仲远那边,是典型的江南诗书门第,讲规矩、重家风,一笔字写得端正,人也清雅。自幼我就记得他一身书卷气,说话慢条斯理,教陆瑛背《诗经》都要配韵脚念。”
“而这许茂许尚书,乃是北方出身,武德起家,从边地一路杀上来的,是真正的朝中骨干。他家里也是官宦世家,不过风格截然不同,讲的是果断刚烈、不让须眉。”
“若这门亲事真能促成……”她语声微顿,轻轻一叹,“那就不仅是两户人家的喜事,而是南北士风的一次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