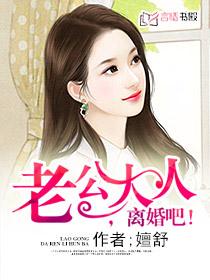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 > 第401章 就该换个法子(第1页)
第401章 就该换个法子(第1页)
“她吴诗雨要查,让她查。我们不配合,没人给她实账、真数,她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查个热闹。”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杜瑛这一关,她过不去。”
说到最后一句,他语调陡然低沉,一字如钉。
那名年轻幕僚还想再劝,正要张口,杜瑛却已抬手制止:“此事休得再议,传我令下去,市舶、盐务、牙行、港管……一律静观其变。她要看,就让她看些假的,别让她找出一条真线。”
众人齐齐点头称是,虽然脸上各有神色,但没人再敢多嘴。
窗外夜风微起,灯火摇曳。
杜瑛拢了拢袖口,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嘱咐身边所有人:“这泉州海贸,岂是她吴娘子说插手就能插的?”
“她来得快,咱们就让她走得也快。”
杜瑛这句话说完,厅内便没了声音,烛火摇曳中只剩他那张稳若泰山的脸,像极了扎根海风中的老树桩。
可另一边,泉州西苑行署的灯却亮得正盛。
厅中几张长案已被拉开,案上铺着厚厚的账本、航线图、通商记录,灯下坐着的,是吴诗雨带来的一众随行亲信:记账的徐兰、擅舶务的陈婉,还有两名南市脚行出身的女役,如今皆换上了干练官袍,一副临阵不乱的架势。
“昭容。”苏妙快步走进来,将一叠新收回的情报放到她桌前,“这是今晚从泉州牙行、小港口、舟行脚夫那边探得的消息,全是第一手。几个脚行在码头守了两个时辰,好不容易才捞到点门道。”
吴诗雨接过细看,眉头越看越紧,但眼底却也慢慢透出一点亮色。
她将一张地图摊开,在泉州港口所在的位置轻轻一点:“果然没错。”
“泉州,是南线海贸的咽喉。往西能通岭南、交趾,再延伸出去就是南洋海道;而东面上船,五日可到琉球,转道东瀛,八日能靠东海诸港。但最要命的不是这些。”
她抬起眼看向众人,语气轻缓,却带着不容质疑的清晰:“是波斯湾。”
陈婉立刻点头,接道:“据我们在牙行查得的信息,大宋每年出口瓷器七成以上由泉州南下转口,再经暹罗、天竺、马六甲等地,最终抵达波斯、阿拔斯。茶叶与绸缎也是此路走得最多。”
徐兰翻出账册:“去年单是泉州出口瓷器就达一百三十万件,茶叶五十万斤,丝绸六十万匹。而这些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由南市女工织坊供货。”
吴诗雨轻轻一笑,却不是得意,而是带着一丝藏不住的锐意:“这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泉州不是地方事,是国策要点。第二,女工织坊,不是附属,是根本。”
厅中安静片刻,苏妙低声问:“娘子意思是……要在泉州设坊?”
吴诗雨点点头,声音低却笃定:“泉州,是南市之外的下一个阵地。”
梁红玉靠着长案,嘴角微扬:“你要真干这事,那杜知府非得被你气得脑仁炸裂。”
“炸就炸吧。”吴诗雨目光明亮,整个人仿佛一下子定了主意,“大宋海贸七成在南,南市织坊要走出去,不能光靠内地转运。女工想掌权,就得自己有货、有人、有出口线。”
她抬头望向满屋女将:“在泉州设坊,设女工、设仓库、设布署,别人的货能从海上出,我们的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