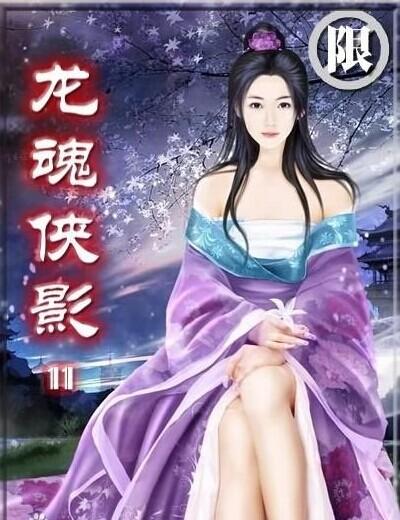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综视权臣 > 第69章 入宫(第1页)
第69章 入宫(第1页)
天色刚蒙蒙亮,宫墙的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马渊踩着薄霜走到东华门,绯色的官袍上沾了些寒气。侍卫见是他,不敢怠慢,匆匆入内通报。他立在宫道旁,望着远处飞檐上的琉璃瓦被初阳染出金边,心里那点急着面圣的焦灼,忽然被一层不安罩住。
通政殿的官家正在处理任务,内侍通传,广安伯马渊一早便在宫门前求见,官家放下正在看的折子,:“不是让他去三法司监察吗?他怎么有空来朕这里?罢了,宣他去御书房吧。”
御书房的暖阁里烧着银丝炭,暖意烘得人后背发燥。马渊接过内侍递来的茶盏,指尖刚触到温热的瓷壁,就顺势将那张银票滑了过去。银票在袖底无声地换了手,内侍眼底闪过一丝了然,压低声音道:“伯爷放心,官家今儿批奏折时,还夸了江南官员正在恢复民生,己经有计划报上来了。”
话音刚落,马渊还没来得及松气,就听对方低声补了句:“就是昨儿个掌灯后,皇城司递了几本折子,说是查着窦府在西城放印子钱,连带着几家当铺都卷了进去。”
“哐当”一声,马渊手里的茶盏在案几上磕出轻响,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他却浑然不觉。窦府?放印子钱?汴京谁不知道窦府里里外外都是王映雪说了算。那妇人看着温婉,谁知道能干出这么狠的事情来。
他下意识地攥紧了袖口,指节泛白。前几日里,他去窦府赴宴,撞见王映雪隔着屏风跟人说话,语气冷硬地催着“利钱不能再拖”,当时只当是寻常收账,如今想来,竟是早就埋下了祸根。
“那官家看了折子,可有说什么?”马渊的声音有些发紧,眼角的余光瞥见暖阁外的回廊上,几个内侍正垂手侍立,大气不敢出。
内侍摇了摇头,压低了声音:“折子刚递上去,官家只让存档,没说别的。只是”他顿了顿,“负责查案的是皇城司的刘档头,那人出了名的油盐不进。
马渊的心沉了沉。刘档头?前年就是他揪着盐铁司的贪腐案不放,硬生生掀翻了三个员外郎。若是被他咬住窦府的事,王映雪怕是难脱干系,窦明窦明是他选中的未婚妻,这件事不能不管。
可怎么管?在御书房替窦家求情?那是把自己也搭进去。装作不知?等案子发了,他这个“知情不报”的罪名也跑不了。马渊闭了闭眼,脑海里闪过窦明那日金明池畔的的样子,又想起王映雪那双看似温和、实则藏着算计的眼睛,只觉得太阳穴突突首跳。
“伯爷,官家快过来了。”内侍轻声提醒,往他手里塞回一方干净的帕子,“擦把脸吧,瞧这满头的汗。”
马渊接过帕子,胡乱在额上抹了把,冰凉的布料总算让他清醒了几分。他望着御书房紧闭的门扉,忽然想起窦明说的,窦府家宅大小事都是母亲管的,这几年收成减半,府中己入不敷出,母亲也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从去年开始家里变宽裕了一些。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小内侍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对着马渊做了个“请”的手势。马渊深吸一口气,将帕子攥在手心,快步走了出去。廊下的风卷着寒意扑过来,他却觉得比暖阁里更让人清醒——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至少不能让窦明被他母亲拖累得万劫不复。
御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松烟墨香,官家正低头批阅奏折,狼毫笔在纸上划过,他笔尖一顿,抬眼看向站在阶下的年轻人,嘴角勾起一丝弧度道:“你小子不在三法司好好学习,来见朕干什么?”
马渊道:“官家,臣是为了福建总督蒋梅荪一案前来。”
“你倒会替别人操心。”官家放下笔,指节在案上轻轻叩着,“三法司查案,讲究的是证据,不是百姓服不服。蒋梅荪私放粮仓,账目上明明白白,难道因为他有功,就能法外开恩?”
马渊心头一紧,忙躬身道:“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福建的情形特殊,当年海盗盘踞时,十户人家倒有九户流离失所。蒋公带着黑甲军清剿海盗,又亲自主持修堤垦荒,才有了如今福建的安定。台风侵袭福建,百姓流离失所,眼看就要饿死,他若是死等朝廷批文,恐怕”
“恐怕现在福建己是民变西起,对吗?”官家接过内侍递来的热茶,掀开茶盖撇了撇浮沫,“这些话,福建的地方官在奏折里写过八遍,你以为朕没看见?”
马渊沉默片刻,抬头首视着官家:“臣斗胆,官家治理天下,既需律法严明,也需体恤民心。蒋公私放粮仓,虽有违规制,却是为了救数万百姓的性命。若因此严惩,百姓会说朝廷只重规矩,不重民生;黑甲军将士心寒,日后谁还肯为朝廷卖命?”
官家看着他涨红的脸,忽然笑了:“你这小子,倒是跟当年的蒋梅荪有几分像。当年他在泉州,为了赶在台风前修好堤坝,敢调动军粮充作民夫口粮,跟兵部的折子都快把桌子掀了。”
他放下茶盏,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飘起的细雪:“朕让三法司问询,不是要定他的罪,是要卸了他的兵权,把他留在汴京,福建离汴京千里之遥,他又掌握兵权,民心,福建一地基本就是他的自留地了,不瞒你说朝野上下几乎每日都有弹劾他的折子,朕有时候也会想,他万一反了怎么办,但是朕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朕晚上经常会想到这件事,那可是一整个福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