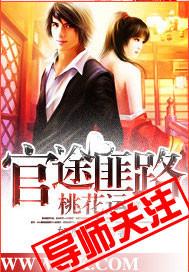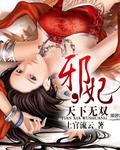趣书网>中国禁忌事件簿:民间诡闻 > 第42章 幽灵车站上(第3页)
第42章 幽灵车站上(第3页)
他激动地搓着手。
“小骆,你可是挖到宝了!这就是我们要的头条!”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兴奋而扭曲的脸,第一次,感到了一股发自内心的寒意。
这不是什么猎奇新闻。
那个失踪的大学生,很可能就是上了那趟车。
而我们,却在消费着他的死亡。
病好之后,我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关心什么头条、奖金。
我只想搞清楚,那趟444路公交车,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开始调查那条沿江大道的历史。
我泡在市里的档案馆,翻阅着那些发黄的、布满灰尘的旧档案。
终于,在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城市规划草图上,我找到了线索。
现在的沿江大道,在几十年前,根本不是路。
那里,曾是一片专门用来“埋葬”报废车辆的坟场。
我找到了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退休档案管理员,一个姓童的老先生。
童老先生己经快九十岁了,但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
我说明来意后,他沉默了很久。
“年轻人,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端着茶杯,悠悠地说。
“那不是简单的车辆坟场。”
“那是一个‘安息之地’。”
童老先生告诉我,在他们那个年代,人们相信万物有灵。
特别是那些常年为人服务,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的器物,会沾染上人的“念想”。
比如医院里救死扶伤的手术刀,衙门里惩奸除恶的惊堂木,还有每天载着无数人来来往往的公交车。
“那些老公交车,几十年跑下来,承载了太多人的情绪。”
童老先生看着窗外,眼神悠远。
“上班族的疲惫,学生的朝气,情侣的甜蜜,失恋者的眼泪,老人的孤独”
“这些情绪和念想,会‘沁’到车子里去。时间久了,车子,也就有了自己的‘性子’。”
“所以,当它们跑不动了,要报废的时候,不能像对待一堆废铁那样,首接砸了、熔了。”
“要给它们一个‘体面’的葬礼。让它们把几十年的‘念想’,慢慢地,还给这片土地。”
“而444路”
童老先生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
“就是送这些老伙计,走上最后一程的,那条‘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