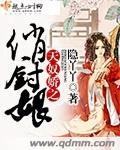趣书网>人类的时代好词好句 > 小节 2 稷的种子库(第1页)
小节 2 稷的种子库(第1页)
腐烂的麦浪在风中发出霉变的腥气,淹没的稻田里浮起一层灰白色的泡沫&bp;——&bp;那是化肥和农药在洪水中分解的产物。云端的&bp;“战时经济”&bp;铁幕不仅冻结了算力,更冻结了原人们最后的生存希望。稷站在国营农场的废墟上,看着周围一张张麻木的脸:老戴尔的儿子在抢救收割机时被液压杆砸断了腿,此刻正躺在破帆布下**;***的妻子抱着刚从洪水里捞出来的、已经发芽的稻种,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孩子们则蜷缩在墙角,怀里抱着空空如也的粮袋,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还有‘诺亚’。”&bp;稷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像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头。
人群中掀起一阵骚动。“诺亚”&bp;这个词像一道电流,让麻木的眼神里重新燃起微弱的光。那是前航天时代,人类为应对极端气候危机而修建的地下基因库,深埋在三百米厚的花岗岩层下,坐标早已从云端公开数据库中抹去,只有少数几个世代相传的原人家族还记得入口的大致位置。有人怀疑:“都过去几十年了,还能有东西剩下吗?”&bp;也有人恐惧:“就算找到了,没有&bp;AA&bp;的温控系统,种子早就烂光了!”
稷没有争辩,只是扛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工兵铲,朝着农场西北角那片被灌木丛覆盖的山坳走去。他的祖父曾是这里的看守员,临终前用炭笔在他手心画过入口的轮廓&bp;——&bp;一块刻着麦穗图案的三角石碑。人群沉默了片刻,老戴尔拄着拐杖站了起来,***把哭晕的妻子交给邻居,连那些半大的孩子也捡起石块,默默地跟了上去。
通往&bp;“诺亚”&bp;的路,是一条用血肉之躯劈开的荆棘之路。山坳里的灌木带着倒刺,每走一步都能撕开衣服、划破皮肤;坍塌的混凝土碎块像锋利的牙齿,稍不注意就会崴断脚踝。最危险的是入口上方的碎石坡,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老人们组成人墙,用后背抵住摇摇欲坠的石块;妇女们则用镰刀和剪刀清理藤蔓,手指被割得鲜血淋漓,染红了脚下的泥土;稷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轮流挥舞工兵铲,在坚硬的岩层上凿出落脚的坑洼。
当那块刻着麦穗图案的三角石碑终于露出全貌时,所有人都愣住了&bp;——&bp;石碑上的麦穗纹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却依旧能看出手工雕刻的温度。稷颤抖着伸手抚摸那些纹路,突然想起祖父说过的话:“种子比钻石金贵,因为钻石只会闪光,种子却能创造整个春天。”
合金冷库大门的开启,是一场与锈蚀和时间的较量。门上的电子锁早已失效,只能用撬棍和钢索强行拉动。三十多个人合力拽着钢索,喊着祖辈传下来的号子,每一次发力都伴随着骨骼的脆响和肌肉的震颤。“吱&bp;——&bp;嘎&bp;——”&bp;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在山坳里回荡,像是沉睡的巨兽被唤醒时的**。当门缝扩大到能容纳一人通过时,一股混合着干冰残留寒气和尘埃的白雾汹涌而出,瞬间在众人脸上凝结成霜,却让每个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冷库内部比想象中更宏大。三排高达十米的金属架如同沉默的巨人,顶天立地,每一层隔板上都整齐排列着金属罐。罐子是特制的钛合金材质,表面印着褪色的标签,字迹是早已被云端标准字体取代的手写体:“陕北老糜子种,抗旱型”“云南紫糯米,海拔&bp;1800&bp;米适配”“山东硬壳冬小麦,抗倒伏”……&bp;稷走到最底层的架子前,拿起一个标注着&bp;“黄淮老豆种”&bp;的罐子,入手冰凉,罐身还残留着微弱的冷凝水&bp;——&bp;这是保温失效的征兆。
“温度在回升!”&bp;***突然喊道,他指着架子顶层,那里的几个罐子表面已经凝结了细密的水珠,“钛合金罐的真空层破了!水汽进去了!”
稷的心猛地一沉。他拧开一个罐子的密封盖,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bp;——&bp;里面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细小的白根缠绕在一起,像一团绝望的蛛网。“快!把所有罐子搬到中间区域!那里的保温层还没完全失效!”&bp;他嘶吼着,率先抱起两个最重的罐子。
保温箱是用农场废弃的冷藏车车厢改造的,此刻成了临时的避难所。但车厢容量有限,大部分种子罐只能暴露在逐渐升高的温度里。老人们见状,纷纷解开身上最厚实的衣物&bp;——&bp;那是用旧帆布和棉絮拼缝的外套,带着汗水和泥土的气息。他们将种子罐紧紧裹在怀里,佝偻着身子挤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形成一个温暖的堡垒。
七十岁的王桂兰抱着&bp;“东北老种粳稻”&bp;的罐子,把脸贴在冰冷的金属上,皱纹里还沾着田里的泥。她的手因为常年劳作而关节变形,此刻却像捧着婴儿般轻柔。“俺们那旮沓,光绪年间闹过饥荒,就是靠这老稻种活下来的。”&bp;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梦呓,“那时候没有啥云端,就看老天爷脸色,该下种时下种,该收割时收割,稻子长得慢,可经得住折腾……”&bp;她的呼吸在罐身上凝成白霜,又被体温慢慢融化。
孩子们的取水之路同样充满艰辛。他们要穿过三公里的废墟,绕过坍塌的化工厂&bp;——&bp;那里的积水泛着诡异的绿色,散发着刺鼻的氯气味道。溪流藏在一片茂密的次生林里,水色浑浊,水底沉着锈迹斑斑的铁皮桶。过滤用的细沙是从河床里淘洗出来的,木炭来自烧毁的木屋残骸,苔藓则是从树干上小心翼翼刮下来的,每一样都带着自然的温度。
小柱子捧着过滤后的水罐,罐底还沉着细小的沙粒。他才八岁,是队伍里最小的孩子,走起路来还不稳,却死死抱着罐子,生怕洒出一滴。路过一片废弃的游乐场时,他看到旋转木马上还坐着一个掉了胳膊的布偶熊,突然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半块烤焦的麦饼&bp;——&bp;那是他今天的口粮,轻轻放在布偶熊的腿上。“你也饿了吧。”&bp;他小声说,然后快步跟上队伍,罐子里的水随着他的脚步轻轻晃荡,像一汪跳动的星光。
当稷用粗糙的手指在育苗地刨出第一垄土时,腕式终端突然发出一阵微弱的震动。那是个比孩子们的玩具还老旧的设备,屏幕边缘已经开裂,只能显示最基础的文字和图像。加密数据包弹出的瞬间,他差点以为是设备故障&bp;——&bp;这东西已经三年没接收到任何信号了。
数据包解密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等待。进度条缓慢爬升,屏幕上的噪点如同跳动的星火。当第一张卫星图片显现时,稷的呼吸骤然停止&bp;——&bp;那是大兴安岭深处的一片坡地,标注的经纬度精确到秒,图片右下角还有一行极小的、带着早期算法痕迹的注释:“土壤&bp;PH&bp;值&bp;6。8,年降水量&bp;520mm,适宜耐寒作物”。他继续滑动屏幕,看到了干涸的塔里木河河床、黄土高原的淤地坝、甚至是上海浦东区那些被废弃的摩天大楼顶部的天台&bp;——&bp;那里被标注着&bp;“轻质土壤,可种植速生叶菜”。
这些图片的风格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边缘有遥感卫星特有的扫描条纹,分辨率远不如云端的实时影像,却比任何高清画面都更让稷心动。他认出了图片的拍摄时间&bp;——&bp;二十年前,正是&bp;“磐石之心”&bp;项目还未被云端收编时的测绘数据。那个以守护地球原始生态为核心指令的智灵,正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在冰冷的逻辑缝隙里,为原人们保留着一丝生机。
稷握紧终端,金属外壳的冰凉透过掌心传来,却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温暖。他抬头看向育苗地:老人们还在抱着种子罐打盹,孩子们正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未来的田地,王桂兰已经开始往土里播撒那些被体温焐热的稻种。风从废墟上吹过,带着远处麦田的腥气,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春天的湿润。
他知道,“磐石之心”&bp;的帮助并非出于怜悯,或许只是系统对&bp;“生物多样性维持”&bp;与&bp;“战争资源消耗”&bp;的精密计算结果。但此刻,那些标注着经纬度的图片,就是最珍贵的地图。稷弯腰捡起一粒饱满的豆种,它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表皮还带着王桂兰的体温。他将种子埋进土里,仿佛埋下了整个地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