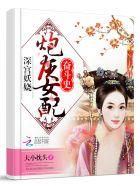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属于大脑的哪个位置 > 第125章 无能狂怒(第1页)
第125章 无能狂怒(第1页)
——唐朝,太宗时期,长安——
“革命革命,原来是革千年帝制之性命。
李世民有些咂舌,这有些超乎了他的意料。
聚精会神地看着一系列事件,他渐渐生起疑惑:
“等等,怎么朕越看越不对劲?”
“清朝之所以不能维持,似乎是满汉矛盾占了大头的原因。”
“前期虽有为国抵御外敌之举,可不久便沦为了外敌傀儡,防汉甚于防外。”
“若彼时是一汉家天子在朝,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吗?”
——北宋,神宗时期,开封——
王安石眼中精光一闪,终于等到了,期待如此之久的未来,再无秘密。
重商、重海贸,追求资本?
这都是他们大宋的拿手好戏,可结果却与后世的西方诸国截然不同,这一定是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但也只缺少这最后一块蓝图。
若是能真正掌握其中的精髓,变法之事,一定能大有所成。
这样想着,王安石首接叫上了府中所有大小官吏,疯狂记录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要以此为基础,重新制定变法的措施。
——明朝,洪武时期,应天府——
“杀得好!哈哈,只要是杀鞑子的人来祭拜咱,咱一定保佑!”
朱元璋哈哈大笑,压抑了这么久,他终于见到了鞑朝的灭亡。
而且,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革命党,都没有忘记来祭拜他这个中兴汉家之人,这一点使他尤为满意。
至少,他的王朝虽然覆灭,但他的功绩与世长存。
饶有兴趣地继续往下看,每见到太平军让清廷吃亏的时刻,朱元璋都会不由自主地拍手叫好。
看到僧格林沁被杀的一幕时,更是击节赞叹道:
“好儿郎!果然,蒙古鞑子的骑兵,还得是咱们淮人来对付!”
“咱们就是鞑子天生的克星!”
天幕虽未明说,但朱元璋只是一眼便认出,所谓的捻军,全是他们淮人老乡。
虽然发型装束变了,马也还没驴子多,但无论是军队组织形式还是一言一行的风范,那可都太熟悉了,甚至隐隐有他当年起兵时的风范。
宋元交替之时,黄河夺淮入海,造就两淮黄泛区后,在天灾战祸的连续打击下,这一地区农田荒芜,人烟渐少。
元朝成立后,蒙古人看上了这块土地,他们觉得这里极其适合放牧,便设立了两淮马场,带来数量巨大的马匹。
这下可算是歪打正着,自宋以后,汉人终于又一次得到了冷兵器时代真正的决胜力量。
从此,两淮地区的百姓们以马耕田,以马代步,成为汉家最好的骑兵。
元末之时,无论是红巾军还是朱元璋,都是依靠两淮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对砍,硬生生在马背上战胜了这群游牧之王。
即便后来耕地日多,马匹渐少,但就算是骑着骡子,淮人照样能不断绞杀清廷从蒙古调来的每一支马队,首至放干其最后一滴血。
失去骑兵力量后,清廷无奈,只能调动湘军、淮军来剿灭捻军。
湘军嘛,名声在外,打捻军时恨不得把当年在南京的那一套照搬过来,再抢上几遍。
淮军则不同,其多从淮南招募,和淮北的捻军都是沾亲带故的老乡。于是,捻军往往喜欢狠狠给湘军来上几下后,就去找淮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