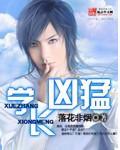趣书网>第二次欧洲世界大战转折点 > 第162章(第1页)
第162章(第1页)
在昔兰尼加,塞努西的顽强抵抗,受到意大利人野蛮手段的对付。绿山地区较肥沃土地上的部落土着被赶出,部落的结构遭到破坏。1933年开始在昔兰尼加大规模移殖意大利农民,在绿山建立了四个村庄;到1940年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地合计已有了二十四个定居点,常住的意大利人共达十万人左右,而且还进一步计划让另外五万名殖民者去那里定居。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在该两地的经济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们修筑了质量极好的道路,有沿着海岸东西走向的,也有从海岸朝南伸向内地的;扩建了港口,勘测了水源并修建了水渠,在本地人的耕作技术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可是,意大利在这里的殖民,是通过从合法拥有土地的本地人手里夺取大片较好的耕地,以及强迫大量阿拉伯居民迁往较贫瘠的土地才实现的。在这方面,意大利对待利比亚居民的办法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在昔兰尼加有所不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是把相当大一部分耕地面积留给利比亚人,而在昔兰尼加,所有较好的土地都被拿去给了意大利殖民者。
第九节多德卡尼斯群岛
意大利应把它在1912年占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希腊,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谈判中从未有人认真反对过,虽然俄国人有一个时候不肯表示同意。对意和约第十四条规定这些岛屿应由意大利割让给希腊,并应成为非军事化。
这些岛屿‐‐斯坦帕利亚岛、罗得岛、卡尔基岛、卡尔帕托斯岛、卡索斯岛、蒂洛斯岛、尼西罗斯岛、卡利姆诺斯岛、勒罗斯岛、佩特莫斯岛、利普索斯岛、西密岛、科斯岛和卡斯特洛里佐岛‐‐上的居民几乎全是希腊族人。1939年,罗得岛上有少数操西班牙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罗得岛和科斯岛上有少数土耳其人,还有少数意大利移民(特别是在罗得岛上)。但其余的居民在语言上和政治感情上都是希腊人,而且都信奉东正教。从1522年起直到1912年止,这些岛民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享受着相当大的地区自治权,在他们祖传的希腊语言方面和希腊民族感情方面没有受到过什么迫害。1912年,意大利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先后夺取了斯坦帕利亚岛和罗得岛,后来又占领了卡斯特洛里佐以外的所有其他岛屿。1912年的意土条约规定土耳其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意大利则撤出上列岛屿。土耳其按时撤出了利比亚,履行了条约义务;可是,到土耳其站在德奥同盟国方面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仍然占领着多德卡尼斯,接着,通过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同协约国缔结的伦敦秘密条约,意大利被许诺&ldo;对其目前占领着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享有完全的主权&rdo;,这一许诺后来在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个敌对国家缔结的洛桑条约的第十五条中得到了确认。
意大利人对待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希腊族臣民,象对待威尼斯-朱利亚和蒂罗尔的南斯拉夫族和奥地利族臣民一样坏,特别是,他们在语言方面执行一条不公正的高压政策,取消希腊语作为当地教育用语和行政用语的合法地位。在多德卡尼斯,意大利语成了法庭正式用语,1937年又被定为正式的教育用语,希腊语课当时只限于在较高级的学校内才得开设。意大利人还企图损害多德卡尼斯的希腊东正教教会,特别是试图使当地教会同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基督教最高教庭脱离关系。
因此,多德卡尼斯应该与希腊王国合并一事,除了因为当地绝大多数居民是希腊族和他们在政治上向往希腊外,还因为意大利统治该岛期间管理不良,使合并更有了理由。
第五编西欧
第一章法国
奇尔斯顿子爵[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955
第一节国家历史性分裂的永久化
第二节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二)共产党的崛起
第三节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第四节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三)第二个回合
第一节国家历史性分裂的永久化
当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8月26日进入巴黎时,人们满怀希望,认为他的到来预示着法兰西不仅将从四年来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将从它过去的一切不幸中解放出来。也许,自贞德时代以来,这个古老国家从未燃起过象这样一种要求全面复兴的真正热情。可是,尽管人们做了大量工作,并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到头来这第四共和国却跟它前面的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多大不同,而更糟的是,那些曾使法国分裂和瘫痪了若干世代的一些旧的分歧‐‐尽管在抵抗外敌时有过暂时的团结‐‐在战争中重新出现了,而且比以往更深,更难弥合。政治图景中所出现的一些变化,与其归因于宪法所设计的任何一种新的体制,不如归因于自从法国第一次革命以来一直在该国活动的那些力量的自然演变和它们的重新组合成为更强大的集团。例如,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战前为数过多的政党缩减成为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ldo;庞然大物&rdo;。的确,这一简化过程迅即发展到这样猛烈的程度,以至不久右派和左派都竞相吸收中间力量中的那些最接近于自己一方的边缘派别,因而促使左右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并且隔着这条鸿沟而相互对峙。但同时,正是由于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那段至关重要的制宪时期中,这些&ldo;巨石般的庞然大物&rdo;是如此势均力敌,而又如此严阵相对,因此新制定的宪法就不可能不是一种妥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