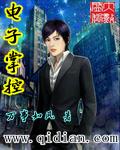趣书网>第二次欧洲世界大战转折点 > 第169章(第1页)
第169章(第1页)
走了这大胆的第一步之后,戴高乐似乎倒退了,他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一个临时的政权是没有资格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这就使左翼和抵抗运动的那些人大失所望,这些人在1945年3月间再次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立即实现结构改革‐‐换句话说,把基本工业收归国有。但戴高乐却把增强国力放在第一位,认为结构改革至少应等到制宪会议选举以后。同时,国家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部长普利文同国民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之间观点有分歧而蒙受损害(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法国总理)。前者倾向于采用&ldo;正统经济学&rdo;的自由放任的做法,而后者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纲领,要采取一些严峻的措施和管制手段来达到经济稳定、加速国民经济恢复的目的。经过长期摩擦之后,孟戴斯-弗朗斯愤然辞职,由普利文接管了他的国民经济部(1945年4月)。这样一来,用真正激进一点的办法来处理当前问题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当地方选举结果表示出很明显的左倾趋势以后,戴高乐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广播中答应在年底前&ldo;作出决定,以便有组织地把煤电等生产的基本工业……以及信贷的管理(通过信贷管理就能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其只能为全民族谋利益&rdo;。同年6月,他向协商会议提出了由国家控制民用航空的建议,7月间又提出了征收资本税和对1940年到1945年间的财产增益课以特种税的两项建议。但甚至这些措施也远未能满足左派方面的要求。勃鲁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报》上写道:法国人民不满意,因为戴高乐&ldo;没有给他们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动纲领和明确的今后目标&rdo;。实际上人们是在责备这位将军没有能更好地适应当时的革命气氛,是在提醒他,群众对他的支持是以他答应要作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诺言为基础的。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迟迟不肯搞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是由于怕冒犯美国工商业界和政界的舆情,从而失掉取得煤、食品、军用品等急需物资的机会。但是,更可能接近实情和更简单的解释则是:第一,戴高乐对经济事务和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他认为重振国家的实力和威望,即他所说的&ldo;上升到强有力的地位&rdo;,是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他梦寐以求的是法国重新成为强国,这就使他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和外交政策上,而经济重建和国内政策则因此而大受影响。他的重整军备政策和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前面已经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则比较成功,同时也较少引起误解。的确,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三大主要目标,是法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都不会不拥护的:法国重新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确保法国今后安全的充分保障;参与世界和平组织。而且,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条件也已充分具备。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萨尔和德国的一部分已划归法国占领;法国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和柏林军事管制总部里都已派有代表,还取得了对柏林一个区的管理权。最后,它又作为五大国之一得到了外长会议上五个席位中的一个,而且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
戴高乐为使他的国家重又成为世界事务中的第一流角色,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力图使它充当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系人或仲裁人。于是,在1944年掌权后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访问,并于1944年12月10日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二十年同盟互助条约。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行动相辅相成的一个步骤,即同英国也商订一项条约,则不得不推迟到英法两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分歧解决之后,而且事实上,直到戴高乐离职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一步骤才最后完成。同俄国缔结的这一条约,除了能堵住戴高乐的那些左翼批评者们的嘴之外,无疑地也是符合于人民大众的总的愿望的。他为恢复法国过去的强国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确,要是他回到法国以后给人留下一点他是受制于另一大国的印象的话,他的声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华盛顿和伦敦关系搞得不那么融洽,以及他在那里以不肯随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于他在国内的处境,因为,法国近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间引起了类似的心情,即那种倔强自信、处处强调独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节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战争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过于政党的性质、各党派的规模、党派的数目等方面的变化了。诚然,法国的政党,同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政党比起来,一向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最显着的一个特色是它们为数很多而每一个都单独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常有人说,在法国,一般的政客都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党应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当选做官的投票者。总而言之,当时确是存在着过多的党派,其名称常常只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标签;这些党派,即使还不是直认不讳的机会主义政党,其据以立党并据以相互对立的东西,往往都是些比较琐细的概念和比较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义或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代表的议会里,当时的政府要确保一个足以进行工作的多数(哪怕只是确保暂时一段时期的多数)的话,就必须在这许多党派之间作成一些交易。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只是调动几个部长,以使议会内各党派各种意见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波动时能有所反映而已。这样,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国宪法体制下行政部门所固有的软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们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无策和更不稳定。不过,其中也有某些与之相应的有利之处。如果说倒阁容易,组阁至少也是很快的。政党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既松散,共同组阁的各党之间的关系也松散,这就有助于培养出那种特别有才华、独立自恃的政客,他们比较地不受党派的束缚,因而在必要时可以对党派间的争议作出仲裁,不费劲地充当联合政府的首脑。这一旧秩序也还有如下一个好处:由于经常有妥协的必要,就不会形成那种庞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团,而那样的集团是很可能会抛弃民主程序而诉诸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这一点,对于一个过去常常发生内讧的国家来说确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