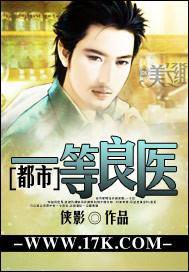趣书网>我有三清道观 > 第13章 暂留澄江清算党羽(第1页)
第13章 暂留澄江清算党羽(第1页)
风很大。
吹在县丞周焕之的脸上,像无数根冰冷的针。
他五十多岁的骨头,在这城楼的风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像是快要散架的朽木。
他不敢看那个站在钱有禄面前的青袍道人。
他只能看着钱有禄。
钱有禄跪在那里,他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筛子,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求饶的声音,只有一些“嗬嗬”的、漏气般的喘息。
“上仙饶命!下官知错了!下官愿献出所有家财,求上仙”
他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那个青袍道人,李常青,只是轻轻地抬了一下手。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周焕之看见,钱有禄那双因为恐惧而瞪得滚圆的眼睛里,瞳孔骤然收缩,然后,扩散开来。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纯粹的、凝固住的空白。
接着,变化开始了。
是从脚下开始的。
钱有禄那双价值不菲的官靴,边缘处,开始模糊。就像水滴落在了一幅未干的沙画上,颜色和线条,开始化开、流淌、消失。
没有声音,没有烟雾,没有光。
就是一种无声无息的、令人脊背发凉的“抹除”。
那“模糊”顺着他的小腿向上蔓延。
裤管、袍角凡是被那无形的力量触及到的地方,都像是被浸了水的泥塑,结构在无声中瓦解。
布料的纹理、刺绣的丝线,都失去了意义,混作一团,然后,归于虚无。
钱有禄还跪在那里,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下往上,一点一点地,被这个世界擦掉。
周焕之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尝到了一股咸腥的血味。
他不敢吐,他怕一丁点的声音,就会让那个青袍道人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
他闻到了一股骚臭。
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大腿内侧,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失禁了,可他感觉不到任何羞耻,只有一种快要被撕裂的恐惧。
最后,是钱有禄的头。
他的五官,像被水冲刷的沙子,鼻子、嘴巴、耳朵迅速地失去了轮廓。最后只剩下那双盛满了空白恐惧的眼睛,在那片模糊中停留了片刻,然后,也散了。
风,吹过。
那件空荡荡的仙鹤官袍,失去了里面的支撑,“呼”的一下,像一张被吹走的废纸,轻飘飘地塌了下去。
“当啷。”
一枚黄铜的县令大印,从空袍的袖口里滚了出来,在冰冷的青砖上,发出一声无比清脆、又无比沉重的声响。
那声音,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周焕之的心上。
李常青看都没看那堆空袍和那枚印信,转身,牵着他的青牛,缓步走下城楼。仿佛他只是来这里,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城楼上,只剩下周焕知,一堆华丽的空袍,和一枚躺在地上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