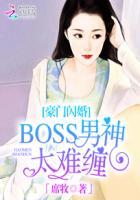趣书网>宅女的异世生活 > 第十一章 兰草的种子要往更远的地方落(第1页)
第十一章 兰草的种子要往更远的地方落(第1页)
金葵奖的奖杯被秦老摆在了片场的旧书案上,黄铜底座映着兰草茶的热气,像给这段日子的奔波镀了层暖光。颁奖礼结束当晚,就有三家影视公司递来合作意向,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诱人——有的说要投巨资拍续集,有的想把谢安的故事改成连续剧,还有人拿着罗森那版“谢安侄女殉情”的剧本找到夏听听,说愿意按她的风格“再改改”。
“改啥改?”张姐把一沓意向书推到一边,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咱们账上刚进了奖金,够拍个新片子的启动资金了。要我说,趁热打铁,再找个好故事!”
沈砚正在给那株从花盆碎片里抢救出来的兰草换盆,闻言抬头:“姑姑的笔记里还记了不少事,有个关于东晋女书法家卫铄的故事,说她晚年在战乱里守着一卷《笔阵图》,临终前把笔法传给了一个放羊娃。”
“卫夫人?”秦老放下茶杯,指节在案上敲出三短两长的节奏,“她的字‘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可史书记载就那么几行。要拍,就得从那些没写进史书的缝隙里找东西。”
夏听听翻开笔记本,扉页上是她刚穿来时写下的“主线任务:文化输出”。那时觉得这六个字像座大山,现在看着案头的奖杯,突然明白——所谓输出,从来不是把故事硬塞给别人,而是先把自己的根扎深了,让土壤里的养分自然漫出去。
正说着,阿Ke举着摄像机跑进来:“听听姐,门口来了个老外,说要见最佳影片的导演。”
门口站着的男人金发碧眼,西装口袋里别着支钢笔,上面刻着“巴黎东方文化电影节”的徽标。“我是电影节的选片人皮埃尔,”他递过名片,中文说得磕磕绊绊,“《淝水之战》里,谢安在门后偷偷开心的镜头,像极了我祖父藏起战争家书时的样子。这种‘不说的懂’,我们想让更多欧洲观众看到。”
他邀请《淝水之战》去巴黎参展,包食宿,还能安排几场映后交流。张姐眼睛一亮:“这可是去国外露脸啊!”沈砚却皱起眉:“他们能看懂谢安的‘屐齿之折’吗?就像我们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总觉得隔着层纱。”
夏听听想起颁奖礼上,罗森擦肩而过时丢下的话:“拍得再好,也就窝里横。老外只认功夫片和宫廷戏。”她摸着奖杯上的纹路,突然笑了:“去。不是为了让他们‘认’,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开心’,可以是藏在门后的屐齿声。”
出发前一周,团队在片场搭起了临时放映室。皮埃尔带了位翻译来,想提前看看片子,顺便讨论映后交流的重点。当银幕上出现谢安站在兰草坡的镜头时,翻译正准备解释“兰草象征君子风骨”,皮埃尔却突然抬手打断:“不用讲,我懂。”
他指着画面里随风晃动的草叶:“我祖母是乡村教师,二战时学校被炸了,她就在麦田里给孩子上课。风一吹,麦穗摇得跟这个一样。有些东西,不用语言。”
夏听听心里一动。原来文化的壁垒,从来挡不住那些扎在土里的共鸣。就像谢安的“不伟大”,皮埃尔的祖母在麦田里的坚守,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力量——在宏大叙事之外,普通人的认真活着。
去巴黎的前一天,罗森的助理又来了。这次没带剧本,而是递来个锦盒,里面是支嵌着红宝石的钢笔。“罗制片说,既然要去国外,总得有支像样的笔签名。”助理的语气少了些傲慢,“他还说……卫夫人的故事要是缺钱,他可以投点,不求改剧情,就想在片尾挂个‘特别鸣谢’。”
夏听听把钢笔还了回去:“告诉罗森,等我们拍出卫夫人的故事,给他留张首映票。”
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时,正是巴黎的清晨。电影节安排的住处临街,推开窗能看见楼下面包店的热气,混着远处塞纳河的风飘上来。沈砚抱着装拷贝的箱子,指尖在箱面上摩挲——那上面贴着片青峰山的兰草标本,是出发前秦老塞给他的。
“秦老说,兰草的种子掉在地上,风一吹,说不定就能在别的地方发芽。”沈砚抬头,眼里映着异国的晨光,“姑姑和陆导当年也想来欧洲参展,可惜片子没拍完。”
首映当天,影院里坐满了人。有研究汉学的老教授,有背着画板的艺术生,还有些是被“东方战场不打仗”的噱头吸引来的普通观众。当片尾谢安站在兰草坡的镜头亮起时,夏听听攥紧了口袋里的兰花钢笔——那是沈曼青用过的旧物,笔帽上刻着朵极小的兰草。
放映结束,掌声比金葵奖时更热烈。皮埃尔带头站起来,手里举着本翻得卷边的《世说新语》:“我一直以为中国历史里都是英雄,原来还有会偷偷开心的宰相。”
提问环节,一个扎着脏辫的女孩举着手:“谢安为什么不告诉别人他很高兴?要是我打赢了仗,肯定要跳起来!”
夏听听笑了,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些感情像兰草的根,埋在土里比开在脸上更有力量。就像这支笔,它写过很多字,可最用力的那一笔,往往藏在纸背。”
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屐齿之折”四个字,用钢笔尖在“折”字上轻轻敲了敲:“这是中国古人的浪漫——天大的喜悦,也能收在一声轻响里。”
交流会结束后,一个白发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颤巍巍地从皮夹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旗袍的女子,手里拿着卷书,背景是巴黎圣母院。“这是我母亲,1937年从南京来的留学生,总说要给我讲卫夫人的故事,没来得及。”老人的声音发颤,“你们要拍她,能……能让我看看剧本吗?”
夏听听把沈砚整理的卫夫人故事笔记递给他。老人戴上老花镜,手指抚过“放羊娃学书法”的段落,突然老泪纵横:“就是这个!母亲说,乱世里最金贵的,是愿意把本事教给普通人的人。”
从巴黎回来时,行李箱里塞满了观众的留言。有人画了兰草,有人抄了《东山赋》,还有个小男孩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谢安的开心,我懂了。”
秦老在片场煮了新的兰草茶,听他们讲巴黎的事,突然指着墙角——那里摆着十几个陶罐,每个罐子里都装着不同地方的土,有巴黎的街心公园,有青峰山的兰草坡,还有沈砚从卫夫人故乡带回的河床土。
“《淝水之战》是把根扎下去,”秦老往每个罐子里撒了把兰草籽,“下一部,就是让种子往远处落。”
张姐拿着新账本进来,脸上的笑藏不住:“国内几家纪录片频道想买《淝水之战》的播出版权,还有个汉服品牌找我们联名,说要做‘谢安同款’屐齿鞋。”她顿了顿,压低声音,“罗森真的投了钱,说这次绝不干涉创作,就想看看‘藏在纸背的力量’能走多远。”
夏听听看着沈砚在陶罐上贴标签,突然想起在巴黎街头看到的一幕——个卖花姑娘把一支兰草插进了凯旋门造型的花瓶里,风一吹,草叶歪歪扭扭地蹭着石雕,像在和历史打招呼。
她拿起摄像机,镜头对准那些刚撒下籽的陶罐。阿Ke调亮灯光,秦老往土里浇了点兰草茶,沈砚的手指轻轻按了按湿润的泥土。画面里,阳光透过老槐树的缝隙落下来,在土罐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极了千年前谢安书案上跳动的烛火。
“开机。”夏听听说。
摄像机转动的声音里,她仿佛听见兰草的根须正在土里伸展的轻响。这声音很轻,却比任何掌声都更让人踏实——因为她知道,有些故事一旦开始生长,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就像青峰山的兰草年复一年地开,就像那些藏在史书缝隙里的心跳,只要有人愿意听,就会永远跳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