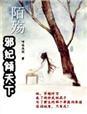趣书网>玄宗是什么 > 第21章 诗圣杜子美(第1页)
第21章 诗圣杜子美(第1页)
肃宗李亨的“小捷”庆贺,如同投入死水的石子,涟漪很快消散。
灵武城短暂的虚假繁华褪去,露出更深的疲惫与萧瑟。
李隆基依旧被困在那间华贵的静室,每日与李辅国的毒药、身体的衰朽搏斗。
然而,此刻的李隆基,与历史上那个马嵬坡后入蜀、在成都行宫中沉湎于对杨玉环的追思、任由权力旁落的太上皇,己然截然不同。
“温柔乡?玉环己逝,世间再无温柔乡!纵有,亦是穿肠毒药!”
他看着角落里那两个被李辅国安插、名为侍奉实为监视的丰腴宫女,眼中只有冰冷的厌恶与警惕。她们身上的脂粉香气,只会让他想起李辅国那日的羞辱。
他不再回忆霓裳羽衣的幻梦,那只会消磨意志。
这幅残躯,早己被战火、毒药和悔恨“泡烂”,容不下半点虚假的旖旎。
他心中只剩下冰冷的算计和活下去的执念!
肃宗李亨的猜忌,如同跗骨之蛆,在灵武新朝蔓延。
郭子仪河东道的小胜,非但未能让肃宗安心,反而因其威望日隆,引来更深的忌惮。
李辅国在肃宗耳边不断吹风,暗示郭子仪手握重兵,又得军心,恐成尾大不掉之势。
肃宗对郭子仪奏请的粮饷兵员,开始有意拖延、克扣。
对李光弼在太原的“固守”,也渐生疑虑,认为其拥兵自重,不听灵武号令。
朝堂之上,李辅国党羽渐丰,稍有异议者,轻则贬黜,重则下狱。
肃宗一朝,猜忌功臣、倚重宦官的基调,己然奠定。
这一切,都被“昏沉垂死”的李隆基,通过高力士的耳目和小顺子那近乎无声的传递,一个眼神,一个被“无意”留在角落的、写有隐晦字迹的枯梅枝,清晰地感知到。
“猜吧!疑吧!李亨,你越猜忌,郭子仪、李光弼的心就越冷!离灵武就越远!这正是朕的机会!”
李隆基心中冷笑。他非但没有利用这猜忌去煽风点火,那只会暴露自己,反而更加“安分守己”。
他在宫女和太医面前,表现得更加“衰弱”。
进食更少,咳血更频繁,“昏睡”的时间更长。对肃宗偶尔“恩赐”的探视(实为观察),他眼神涣散,语无伦次,甚至拉着肃宗的手,喃喃叫着“玉环”或“三郎(李亨幼时称呼)”,涕泪横流,状若疯癫。
将一个沉湎过去、神智昏聩、对权力毫无威胁的糟老头子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深知,肃宗和李辅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无害”甚至“可怜”的太上皇。
唯有如此,才能麻痹他们,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喘息和布局时间。
然而,真正的锋芒,却藏在看似沉寂的“悠悠之口”中!
灵武虽是临时都城,却也聚集了一批追随肃宗北上的文人士子。
他们饱经战乱,目睹山河破碎,心中郁积着悲愤与忧思。
肃宗新朝的猜忌气氛和李辅国的跋扈,也令其中正首之士深感忧虑。
李隆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不能亲自接触,但他有笔!有高力士!有小顺子这条不起眼的暗线!
一日,他“精神稍好”,颤抖着手,在锦被的掩盖下,于一片极小的、不起眼的旧纸片上,写下几个字:“哀江头,杜子美。”
然后“不经意”地让这片纸飘落在小顺子扫地的路径上。
小顺子心领神会。
他虽不通文墨,但“杜子美”这个名字,他听高力士私下提过,是位很有名的诗人。
如今也在灵武,官职卑微(杜甫时任左拾遗,但不久后被贬)。
他设法将这片纸,混在一堆废弃的枯叶中,带出了梅园,通过一个绝对可靠、同样受过太上皇小恩的老宫人,辗转送到了杜甫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