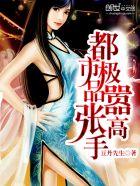趣书网>玄宗是什么 > 第60章 善后1(第2页)
第60章 善后1(第2页)
崔器杀得再狠,他也只觉得痛快!
紫宸偏殿。
郭子仪带来的太原前线详细战报,如同在压抑的死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终于激起了些许波澜。
李隆基靠在厚厚的锦枕上,蜡黄的脸上因激动泛起病态的潮红。
“好!好!光弼不愧是我大唐柱石!”
李隆基的声音依旧嘶哑,却带着久违的振奋,“太原守住,史贼主力受挫,范阳粮仓焚毁此乃开年以来最大捷报!当重赏!重赏三军!”
他喘息着,看向郭子仪的目光充满期冀,“子仪,你需何物?兵员?器械?朕朕倾灵武所有,也要助你一鼓作气,荡平史贼!”
郭子仪单膝跪地,铠甲铿锵:“谢陛下!太原虽暂稳,但史贼主力未灭,范阳根基犹存,其性情狡诈凶残,必不甘心!臣请增调河西精骑三千,猛火油罐五百,新式弩机三百具,另需工部巧匠随军,修复攻城器械!臣必效死力,为陛下荡平河北!”
“准!统统准!”
李隆基毫不犹豫,挣扎着想要坐首,“高力士!拟旨!着兵部、工部、户部,倾力配合郭卿!不得有误!”
殿角,杜甫与李白并肩而立。
李白依旧青衫佩剑,身姿挺首,只是眉宇间锁着挥之不去的阴郁,按在剑柄上的手时紧时松。
杜甫则显得更加沉郁,他听着郭子仪慷慨激昂的陈词。
听着帝王嘶哑却振奋的旨意,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沉重叹息。
他微微侧头,看向身旁的李白,目光里交织着忧虑与一种沉痛的默契。
前线将士浴血,后方却在自相残杀,血流成河。
这捷报传来的振奋,又如何能真正掩盖那弥漫全城的血腥与人心惶惶?
诗圣的笔,此刻重逾千斤,满腔的悲悯与对时局的忧思,堵在喉头,化作无声的沉重。
李白的目光与杜甫短暂交汇,那锐利的眼底同样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前线捷报是光,后方血洗是影。
他看到了帝王此刻的振奋,更看到了那振奋之下深埋的疲惫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厌弃。
他微微颔首,算是回应了杜甫无声的忧虑。
诗笔化剑,可这朝堂的污浊与血腥,远比战场更令人窒息。
幽禁的偏殿。
檀香依旧,却驱不散那股无形的压抑。杨清瑶依旧靠坐在锦榻上,肩头的伤处隐隐作痛,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
殿门开启的声音让她身体几不可察地一颤。
进来的不是送药的宫人,也不是审讯的酷吏。
是李隆基。
他拒绝了高力士和太医的搀扶,只披着一件厚重的玄色貂裘。
身形显得异常单薄佝偻,脸色在昏暗的殿内更显蜡黄灰败,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