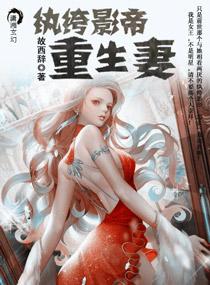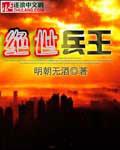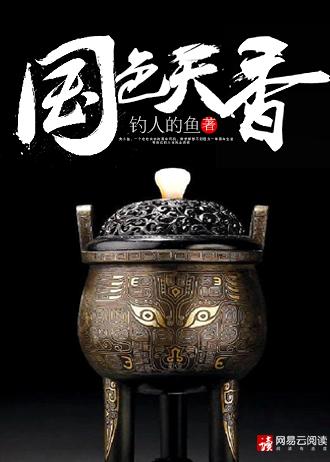趣书网>北宋千年龙虎榜状元 > 第15章 进宫面圣(第2页)
第15章 进宫面圣(第2页)
但方才那惊鸿一瞥,己足够他勾勒出一个印象:平和的面容,眼角的细纹透着操劳,眼神平静却深邃,仿佛能洞悉人心。
这便是大宋仁宗皇帝,赵祯。
“抬起头来。”赵祯的声音依旧温和。
沈瑜缓缓抬头,目光依旧微垂,保持恭敬,但己能看清御案后的帝王。
赵祯也在打量他,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沈瑜,”赵祯缓缓开口,手指轻轻敲了敲御案上放着的一个锦盒,盒盖打开着,里面正是狄咏献上的那几块沾着酒精痕迹的琉璃碎片和那只破碗,“狄青之子奏称,此物名为酒精,乃你取酒之精魄所炼,有祛毒疗伤、活人无数之奇效。他以身试之,效用非凡。更言此物于边军伤患,乃不世祥瑞。”
赵祯的声音顿了顿,目光如实质般落在沈瑜脸上:“朕很好奇。你一介寒门书生,如何通晓此等精微造化之术?此物效用,真如狄卿所言,非虚妄?”
来了!核心拷问!
沈瑜心念电转,现代的灵魂在此刻高速运转。
他再次躬身,声音清晰,带着一种源自知识本身的笃定:“回官家,学生不敢妄言通晓造化。此法灵感,源于医道典籍中火酒驱寒避瘴、清洗污秽的零星记载,以及格物致知之理。”
他巧妙地避开了“前世知识”,将源头引向古代医书和儒家推崇的“格物”:
“学生曾思忖,寻常酒水驱寒尚可,用于伤口却易致溃烂,盖因其性浑浊,杂质繁多。遂想,若能将酒水反复提纯,取其最清最烈之精华,或可祛除引致溃烂之邪毒?此念一起,便反复试验,幸得狄公子鼎力相助,提供器具匠人,方侥幸得此酒精。”
“祛除杂质,就像制盐法那般?”赵祯问道。
宋朝便己经有了精盐,用石灰乳等化学物质帮助沉淀和去除盐水中的杂质。
沈瑜指向锦盒中的碎片:“其效用,狄公子以身试法,足证其烈其纯。学生斗胆进言,此物若能量产,配发边军,用于伤兵创口清洗,辅以干净布帛包扎,必可大幅减少伤口溃烂化脓、高烧不治之惨况!此非学生之功,实乃天佑大宋,假学生之手,献此活命祥瑞!”
沈瑜将功劳归于“天佑”和“格物致知”,既显得谦卑,又拔高了立意,更巧妙地强调了“量产”和“配发边军”的实际价值。
他语气恳切,目光坦荡,那份源自现代人对科学原理的绝对自信,让他即使在帝王面前,也透着一股沉稳的底气。
赵祯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锦盒的边缘。
他阅人无数,能感觉到沈瑜话语中的真诚和那份奇异的笃定。
这“酒精”的价值,在他心中己有了分量。
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赵祯的目光从锦盒移开,再次落到沈瑜身上,那温和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深沉的探究:
“此祥瑞之功,朕记下了。擢你为承务郎,便是酬功。”
他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深沉,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威压,
“然,汴河之事,你又当如何自处?”
沈瑜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别说是在宋代面对着皇帝了,这哪怕是在现代,你面对着被你打了屁股的女子的父亲,你也不可能稳住心神啊。
“官家明鉴!”沈瑜的头压的更低了。
“汴河之事,学生不敢辩驳。当时冰水刺骨,公主危在旦夕,学生救人心切,唯恐公主挣扎过甚,双双殒命,情急之下,行止确然逾矩失当,冒犯公主天颜,罪该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