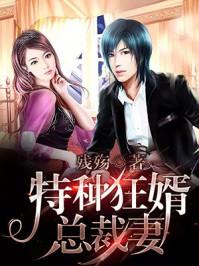趣书网>北宋千年龙虎榜状元 > 第84章 抄个菜谱不过分吧(第1页)
第84章 抄个菜谱不过分吧(第1页)
川蜀道,眉州,皇祐六年八月末。
哦不对,现在仁宗己经改元至和了,应当是至和元年。
囚车则是由狄青派人负责押送。
将泼天的功劳让渡给狄青,沈瑜心中并无半分不舍。
他深知,自己这个幸进的驸马加皇子养兄,根基太浅。
而他沈瑜,更看重的是此行的真正收获,打开了局面,积累了资本,更重要的是。
兑现了对赵徽柔的承诺,活着回来了。
使团离开大理国境,进入川峡西路。
嘉州(今乐山)渡口,岷江与大渡河在此汇流,江面开阔,舟楫如梭。
沈瑜一行在渡口旁的茶肆歇脚,等待过江的客船。
茶肆简陋,却坐了不少南来北往的旅人,喧嚣嘈杂。
沈瑜正捧着一碗茶解渴,忽听邻桌传来一阵争论声。
“《战国策》固然奇诡雄辩,然过于重术轻道!苏秦张仪之徒,朝秦暮楚,翻云覆雨,虽逞一时口舌之利,终不免身死名裂!岂是君子所取?”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子由此言差矣!”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语速更快,带着锐气飞扬,
“纵横之术,亦是大道!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以三寸不烂之舌息百万之兵,解生民倒悬,岂不胜过腐儒空谈仁义?至于苏张结局,乃其术未臻至境,贪恋权位所致,非纵横之道本身之过也!”
沈瑜连忙循声望去。只见邻桌坐着两个年轻士子。
一人约十七八岁,身着青衫,正是方才反驳《战国策》的子由。
另一人年纪稍长,看着也就十八九岁,顾盼间神采飞扬,此刻正挥舞着手臂,为自己的论点据理力争,正是那个为纵横家辩护的子瞻。
川峡西路,子瞻子由,仁宗至和年间。
沈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差点被口中的茶水呛到。
千古文豪,东坡居士!还有他那位沉稳持重的弟弟苏辙!
竟然在这嘉州渡口的破茶肆里,让自己撞上了?
沈瑜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和穿越者面对偶像的奇妙心态,放下茶碗,整了整衣冠,起身走到邻桌,对着争论中的两人拱了拱手。
“二位请了。在下汴京沈瑜,适才听二位高论,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心向往之。尤其是这位兄台,”
他看向苏轼,“为纵横家鸣不平,见解独特,敢问高姓大名?”
苏轼正争论在兴头上,见有人搭话,还是个气度不凡,自称来自汴京的年轻人,顿时来了兴趣。
他起身还礼,动作洒脱:“在下眉山苏轼,字子瞻。这位是舍弟子由,苏辙。”他指了指旁边的沉稳少年。
苏辙则是起身,一丝不苟地行礼:“苏辙见过沈兄。”
同时暗暗提醒一旁的苏轼。“当时研发酒精和香水的沈驸马吧?”
“原来是苏氏昆仲!久仰久仰!”
其实每次沈瑜对人说久仰,都是毫无客套之意而是发自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