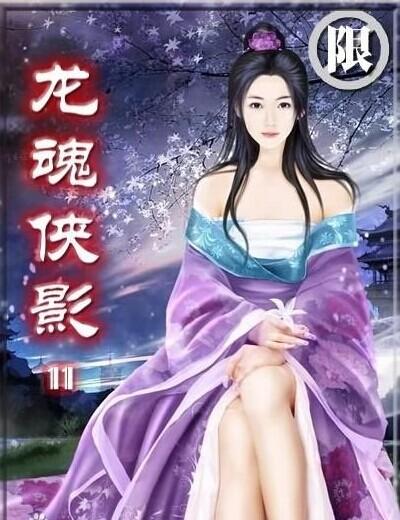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双生魂种 > 寓言故事99(第9页)
寓言故事99(第9页)
阿楚和晏辰也没闲着,他们帮鲁班改进了伞的设计,比如加上伞柄的防滑纹路,在伞面涂上防水的油脂等。
阿楚发现,鲁班不仅会做木工,还懂很多物理和数学知识。
他能精确地计算出每根伞骨的角度和长度,让伞面既美观又结实。
“这家伙要是生在现代,绝对是个顶级工程师,”阿楚感慨道,“说不定还能拿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可没有木工奖,”晏辰调侃道,“不过他的发明确实改变了世界。”
离开鲁班家的那天,鲁班送给他们一把特别精致的伞,伞面上还刻着花纹。
“这把伞送给二位,”鲁班真诚地说,“多谢你们的帮助,没有你们,我做不出这么好用的伞。”
阿楚接过伞,发现伞柄上刻着一行字:“道法自然,匠心独运。”
她忽然明白了,鲁班发明伞,不仅仅是观察荷叶那么简单,更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所谓的灵感,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
走出很远,阿楚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鲁班还站在门口向他们挥手,手里拿着那把最初的伞,在雨中显得格外挺拔。
“你说,他以后还会发明什么?”阿楚好奇地问。
“谁知道呢,”晏辰撑开伞,将她护在伞下,“但我相信,他会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和热爱。”
雨还在下,但阿楚觉得心里暖暖的。
原来,改变世界的,往往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观察和思考。
泥土混合着铜锈的味道钻进鼻腔,阿楚揉着被撞疼的额头,发现自己蹲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四周堆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零件,有铜环、齿轮、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刻度盘。
“这是哪儿啊?”阿楚站起身,不小心碰掉了一个铜球,“叮铃哐啷”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嘘,”晏辰捂住她的嘴,指了指不远处那个正在画图的老者,“看那图纸,像是地动仪的结构,我们应该是在张衡这儿。”
阿楚点点头,果然看见老者画的图纸上,有一个类似酒樽的器物,周围刻着八条龙,嘴里都衔着铜球。
“原来地动仪长这样,”阿楚小声说,“比课本上画的复杂多了。”
“课本上的只是示意图,”晏辰解释道,“真正的地动仪内部结构很精密。”
张衡显然没注意到他们,他全神贯注地画着图,时不时拿起零件比划一下。
阿楚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专注的神情,忽然觉得有些敬佩。
“在那个年代就能想到测地震,太厉害了,”她感慨道,“不知道这玩意儿真的管用吗?”
“应该管用,”晏辰拿起一个铜珠,“你看这重量和大小,刚好能卡在龙嘴里,一旦有震动就会掉下来。”
张衡画完图,开始组装地动仪,但试了几次都不理想,铜珠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掉下来。
他皱着眉头,显然很苦恼。
“是灵敏度的问题,”晏辰忍不住说道,“需要调整杠杆的角度和重量。”
张衡吓了一跳,这才发现房间里多了两个人。
“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他警惕地问。
“我们是路过的学者,对先生的发明很感兴趣,”晏辰拱手作揖,“刚才多有冒犯,还望海涵。”
张衡打量了他们一番,见他们不像坏人,也就放松了警惕:“你们懂这个?”
“略懂一些力学原理,”晏辰指着地动仪,“先生的想法很巧妙,但杠杆的支点太灵敏,容易受到干扰。”
他一边说一边调整了一下杠杆的角度,又在末端加了个小铜块。
“这样试试,”晏辰示意张衡,“轻微的震动不会触发,但强烈的地震就能反应。”
张衡半信半疑地试了一下,果然,轻轻晃动桌子,铜珠没掉下来,但用力一震,铜珠就“当啷”一声掉进了下面的蟾蜍嘴里。
“成了!”张衡激动得手都抖了,“太厉害了!你怎么想到的?”
“只是一点小技巧,”晏辰谦虚道,“主要还是先生的设计巧妙。”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帮张衡完善了地动仪的设计,比如增加了刻度,能更精确地判断地震的方向,还在底部加了减震的装置,减少误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