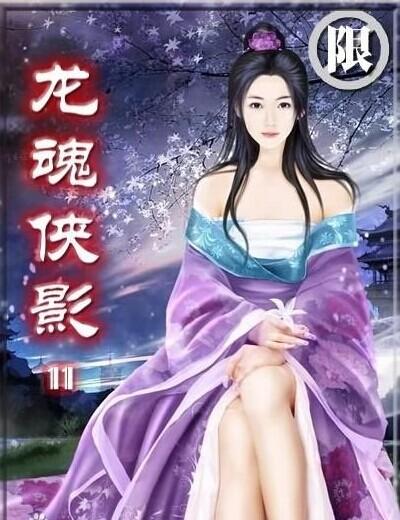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严党和清流党 > 第366章 贡院(第1页)
第366章 贡院(第1页)
嘉靖三十三年春·贡院
春寒料峭,贡院朱漆大门前的石狮子上还凝着薄霜。
陈恪勒住缰绳,枣红马打了个响鼻,喷出的白气在晨光中迅速消散。
他身后跟着一队锦衣卫和户部吏员,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打破了贡院街清晨的寂静。
“靖海伯到——”
门房老吏早已得了消息,颤巍巍地打开沉重的院门。
陈恪翻身下马,绯色蟒袍的下摆扫过门槛,带起一阵微尘。
他目光扫过这座承载了无数士子梦想与失意的建筑,四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实现了阶级跃迁。
故地重游,心境却已天壤之别。
主考赵贞吉已在明伦堂等候,见陈恪进来,微微颔首:“子恒来了。”他指了指案上堆积如山的卷宗,“锁院已毕,出题翰林们皆已入闱,由锦衣卫严加看守,内外隔绝,饮食皆由专人递送,直至考题拟定,火漆密封,呈递御前。”
陈恪点头,这是大明科举的铁律。
十数位翰林学士被集中关在贡院深处的小院,断绝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潜心拟题。
最终定下的题目会用多层油纸包裹,加盖火漆大印,由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亲自送入西苑。
嘉靖帝通常不会提前拆看,以示对“天意”和“文运”的尊重,只待考试当日,在百官见证下当众启封。
除非皇帝有特别旨意,才会提前告知出题方向。
“赵部堂辛苦。”陈恪拱手,“考场布置如何了?”
赵贞吉捋了捋花白胡须,看向一旁的赵文华:“文华,你领了巡查号舍的差事,进展如何?”
赵文华脸上堆起惯常的谄笑:“回部堂,下官已巡视过东区号舍,一切妥当。只是…”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下官这几日偶感风寒,头重脚轻,恐难胜任这需细致巡查的繁重之务。西区号舍,不如…”他目光瞟向陈恪,意思不言而喻。
陈恪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声音清朗,毫不客气地戳破:“赵侍郎一贯只挑轻松的活干,倒也难怪。无能之辈,确也不能勉强。”
“你!”赵文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随即涨得通红,眼中射出羞愤交加的光芒,手指着陈恪,气得嘴唇哆嗦,“陈子恒!你…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官为国操劳,为君分忧,岂容你如此污蔑!”
陈恪却看也不看他,径直对赵贞吉道:“部堂,西区号舍的巡查布置,交由下官便是。赵侍郎既‘偶感风寒’,还是回府静养为宜,免得过了病气给即将应试的举子,误了朝廷抡才大典。”
他特意在“偶感风寒”四字上加重了语气,讽刺意味十足。
赵文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陈恪的“你”字卡在喉咙里,半天说不出下文。
他实在想不通,这陈恪怎么像吃了火药一样,处处针对自己?
他哪里知道,陈恪骨子里最厌恶的,正是他这种毫无原则、只知攀附权贵、遇事推诿的官僚蠹虫。
陈恪不再理会身后气急败坏的赵文华,向赵贞吉略一拱手,接过副考官的印信和名册,转身便带着自己的随从和分派给他的几名户部小吏、锦衣卫,大步流星地向贡院西区走去。
穿过熟悉的龙门,走过长长的甬道,眼前豁然开朗。
一排排低矮的号舍如同蜂巢般整齐排列,在初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肃穆。
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墨香、木头腐朽以及淡淡石灰水的混合气味。
四年前,他就是在这里,于万千士子中杀出重围。
如今故地重游,身份已从考生变成了考官,心境确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
“各房号舍,逐一检查。”陈恪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地面、墙壁、号板、桌椅,有无夹层、暗格、刻字。缝隙角落,尤其留意。凡有可疑之处,即刻记录,着人修补清理。”
“是!”众人齐声应诺,立刻分散开来。
这工作确实如陈恪所想,繁琐至极,枯燥乏味。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一间间检查过去,不能有丝毫马虎。
陈恪并未端坐明伦堂,而是亲自巡视。
他步履沉稳,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过每一寸可能藏污纳垢的地方。
手指不时敲击号板,倾听是否有空洞回响;俯身查看桌腿缝隙,检查是否有夹带遗留的痕迹;甚至用指甲刮蹭墙壁,看是否有新近涂抹掩盖的刻字。
他走过一排排寂静的号舍,仿佛走过自己曾经埋头苦读的时光。
号板冰冷坚硬,桌面斑驳,刻满了不知多少届考生的焦虑与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