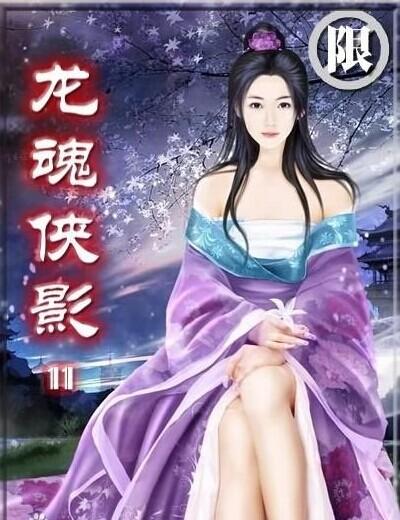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严党和清流党 > 第370章 考官篇四(第1页)
第370章 考官篇四(第1页)
嘉靖三十三年春·贡院阅卷所
贡院深处,阅卷所门窗紧闭,隔绝了春日最后一丝喧嚣。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墨香、新纸的草木气息,以及十数位阅卷官员身上散发的、混合了疲惫与专注的独特味道。
巨大的案几上,朱卷堆积如山。
这些并非考生的亲笔,而是由誊录所的书吏,用朱砂笔一笔一划重新誊抄的副本。
墨卷即考生原卷则被糊名封存,严密保管。
这便是明代科举的核心防弊制度之一——糊名誊录制。
任你笔迹龙飞凤舞或是娟秀工整,到了考官手中,都变成了统一、工整、无法辨认来源的朱砂字迹。
考官面对的,只是一篇篇匿名的文章,最大程度避免了人情请托与笔迹辨认带来的不公。
陈恪坐在案几后,第一次以考官身份参与这浩大的工程。
他面前摊开一份朱卷,指尖无意识地捻着腰间常乐那只失而复得的香囊,试图驱散连日埋首带来的眩晕感。
他虚心聆听着旁边一位老翰林慢条斯理的经验之谈:“……伯爷请看,这誊录之制,实乃防弊之良法。笔迹既不可辨,考官便只能以文取士。然誊录书吏亦需严查,防其受嘱换卷,或故意誊错……”
老翰林须发皆白,声音平和,带着阅卷多年的从容。
陈恪微微颔首:“多谢前辈指点,此法确为公允之基。”
他目光扫过堆积的卷山,深知这“公允”背后是海量的工作。
每一份朱卷,无论优劣,都要经过至少两位考官之手,甚至更多。
这便是轮房制或称轮阅制。
“一份卷子,若某房考官未取中,标记‘落’或‘下’,亦不可轻易丢弃,”另一名中年考官接话,指着案头不同区域的卷山,“它需流入‘未取卷’池中,由他房考官轮番覆阅。如此,即便某位考官因个人喜恶一时‘走眼’,亦有机会被他房考官慧眼识珠,不至于明珠暗投。”
“正因如此,我等才需如此殚精竭虑啊。”陈恪感叹,目光再次落回眼前的卷子。
工作量之大,令人望而生畏。
考生虽都是举人,但学识水平参差不齐得令人咋舌。
特别是策论题——嘉靖皇帝亲定的“海禁”之议,明显是在测试天下士子对国策的见解与倾向。
陈恪看得眉头紧锁。
大多数文章,要么是泥古不化的祖制扞卫者,引经据典痛陈开海之祸,言辞激烈却空洞无物;要么是盲目鼓吹开海通商,描绘黄金万两流入的美梦,却对如何应对倭寇、管理贸易、平衡财政等实际问题避而不谈,或言之无物。
真正能客观分析利弊、提出切实可行方略者,寥寥无几。
“百无一用是书生,此言……”陈恪心中暗叹,后半句咽了回去,只是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强打精神继续批阅。
就在这时,一个带着几分刻意炫耀的声音在陈恪案边响起:“靖海伯初次阅卷,想必劳神。本官倒有些心得,这判卷呐,首重立意,次看文采,最后才是经义贴切与否。尤其这策论,须得……”
赵文华踱步过来,脸上堆着“前辈”式的笑容,显然是想抓住这个陈恪“不懂”的领域,好好秀一把资历。
陈恪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没听见他的话,目光专注地落在新一份朱卷的起首几行。
他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案几,示意旁边侍立的书吏将下一份未取卷递过来。
动作自然流畅,完全无视了赵文华的存在和即将开始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