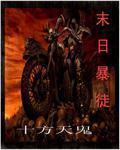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209章 先见之明(第2页)
第209章 先见之明(第2页)
仁忠也不废话,抬手递过一封黄纸密诏,语气压低,几乎藏着火:“陛下刚刚决定,派我出使临安。”
幕洧眉心一动,指尖略一顿,接过那封密诏细细扫了一遍,神色终于有了变化。
“正式通宋?”他念了一句,“这么多年了终于要走这一步了。”
“对。”仁忠长出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大宋是你出生的地方。”他语气微顿,望向幕洧,“这次,我要去临安,你愿不愿与我同行?”
幕洧没有立刻答话,而是静静地看着手中那封密诏,眼神缓缓变得深远。
他在西夏官场浮沉二十余年,从一个流亡的汉人,做到今日枢密使之位,谁都以为他早已断了故土之念,骨血之情。
可此刻,他心中那些压了多年、不敢碰的东西,却突然间被人一刀剖开。
“殿下。”他轻轻开口,语调压得很低,“我出生在扬州,幼年逃亡,被金人围城,父母死于乱兵之手,是西夏收留了我,把我养大,教我读书,让我能入朝为官。我的命,是西夏给的。”
他抬起头,语气中透出一种夹在两国之间的冷静与决然:“但我也是宋人,骨子里是改不了的。”
“若如今真有机会,以我之手,促成西夏与大宋的交好,让两国停战、通使、互信”他说到这里,嘴角微扬,眼中难得闪出一抹炽热,“那将是我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仁忠凝视着他,一字一句道:“那你愿意随我出使?”
幕洧没有犹豫,点头:“我愿意。”
两人对坐,茶已凉,言犹在耳。
这一晚,濮王府书房中的灯,亮到了后半夜。
仁忠心中很清楚,这一趟出使,看似是一次邦交修复,实则是给赵桓送去试探与投名状,能让宗翰吃瘪、让金国南线折戟、让宗泽、韩世忠都愿赌性命的人绝不会是个可以轻慢之人。
“这位赵桓,怕不简单。”仁忠低声道。
两人对视一眼,眼神中皆有慎重,也有期待。
而此时,万里之外,临安皇宫。
午后的阳光洒落在宫墙斜檐,微风拂过绿意新上的宫苑,一丝茶香弥漫在内殿之中。偏殿里,赵桓斜靠在榻上,手里捏着一枚还未泡的龙井叶子,听着史芸在对面滔滔不绝地讲述她这阵子的织坊大计。
“总之,一切都顺利得不像话。”史芸坐得笔直,神情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前头几批女工刚上手那会儿,确实有点磕绊,但我们派了教坊旧人去做基础培训,教得又细、又快。”
“现在各地织坊的女工已经能独立完成流程了,从纺线到配色,再到整经入机,全都能一气呵成。”她说着,嘴角带笑,明显颇有成就感。
赵桓斜睨了她一眼,笑道:“说得这么神,搞得我像在听哪位织娘成仙了。”
“那可不是仙,是能赚钱。”史芸也不客气地接了话,挑了挑眉,“陛下你不一直说嘛,光是救济不是长久之计,得给老百姓找出活路。我现在就给你找了这么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