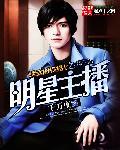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250章 我得问问他(第2页)
第250章 我得问问他(第2页)
可赵构那天在州署里,亲自拍着他的肩膀,说:“孙大人,岳州这盘棋,你只要替我稳住,不出半年,我便让你平步青云。”
“将来朝中你若想入政事堂,我赵某人保你一个位子。”
说这话的时候,那人风度翩翩,眼神沉着,看上去比任何文臣都稳。
但现在,他看着眼前这堆关于百姓如何被逼流离失所的报告,忽然有点想问一句:那所谓的位子,是不是拿人命换的?
孙廉闭了闭眼,低声道:“罢了。”
“给我备马,我要去见赵殿下。”
田鹤一惊:“大人,您是”
“我得问问他——”孙廉语气平静,像一潭水,却有底潮在动,“到底这岳州是要屯粮,还是要死人。”
“若是为了升官,要我也昧下去,那我真干不下去了。”
他说完,轻轻叹了口气:“老百姓穷可以苦,官可以贪,但不能连条命都没了。”
“再这样下去,出事的,不只是百姓。”
“是整个岳州。”
岳州东郊,临江别院。
这处宅院原是前任郡守避暑之所,山水相拥、庭院幽深,如今却被赵构借居已有月余。院中人虽不多,但调度有序,从吏员、侍从到账房商贾,全是熟面孔。
辰时未到,孙廉便已快马抵达。
一身官服未解,满脸风尘,立于堂前拱手:“孙廉,求见赵殿下。”
片刻之后,内侍出迎:“殿下吩咐了,大人请。”
厅中,香炉袅袅,赵构着一身便服,正翻着一卷地图,旁边是一沓地契副本。
他抬头,见人来,唇边笑意不减:“孙大人风尘仆仆,一大早就来,怕是有事?”
孙廉拱手:“殿下,属下确有一事,不敢延误。”
“说。”
孙廉不绕弯,直接道:“洞庭湖一带,圈地之风愈演愈烈。已有数十村民联名呈状,言周家、何家强占良田、水东、漆湾多处村寨拆迁无期,流民困苦,疫疠初显。”
“今日我不绕文书,只问一句:殿下,这事我们还要继续推下去吗?”
赵构神情未变,手指翻着桌上文卷,语气却慢条斯理:
“继续,自然是要继续。”
“这是朝廷既定之策,岳州地沃水广,不屯粮,何以支北战?洞庭不稳,大后方难安。”
他说着,抬眼,嘴角微翘:“至于一些扰民的声音嘛孙大人你是明白人,想成大事,怎能在意这些细枝末节?”
孙廉站在原地,眉头一皱:“可百姓确是困苦。”
“洞庭水灾三年,生计全靠湖边几亩薄田。如今圈地毁村,他们何以为生?”
“若是真为屯粮,属下无话可说,可如今许多地契却落在了商贾之手,连民粮也开始设限,那些赵氏漕运、王陈粮坊,真的是朝廷派下来的?”
赵构听到这,动作略顿,但神色依旧镇定。
他放下卷轴,坐直了身子,语气平静:“孙大人,你我是读书人,也都做官多年,知晓世道。”
“粮从何来?兵从何来?朝廷若不给,咱们总不能空着手等人来打吧?”
“这些商号确实借了我名,但他们也出了钱,买了地、运了粮,收了一点民间旧田不假。”
“可归根结底,目的是一致的,支战和稳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