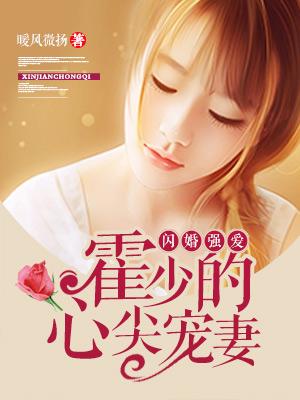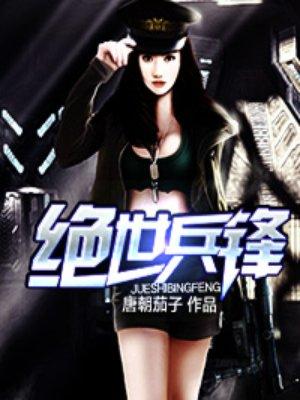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252章 内幕(第1页)
第252章 内幕(第1页)
“赵构不是个简单人,他太稳了,稳得我看不透。
秦喆沉吟片刻,忽然开口:“孙兄,我在临安前几日,还在户部听人提起过圣上。”
“你知道圣上如今最重视什么?”
孙廉没吭声。
“整军、清吏、改革科举。”秦喆慢慢道,“如今京中各部都在说,新帝手腕刚、目光准,是几十年来难得的明主。”
“你说这么一个皇帝,会在这种节骨眼上,派人来圈地逼民?”
他顿了顿,盯着孙廉:“说实话,若不是你说是赵构亲口称陛下命令,我根本不信这是圣上的旨意。”
“圣上不像会干这种事的人。”
孙廉静静听完,半晌没说话,酒香渐淡,桌上菜也凉了。他低头,看着手里那碗酒,忽然轻轻道:“我也不信。”
秦喆看着他,眼神越发凝重,忽地低声道:“那你可想过一个问题?”
孙廉抬头,神色疑问。
“就算,我是说就算,陛下真的在暗中默许这场圈地,真要推行这件事,”秦喆慢慢说,“他也绝对不会让赵构来干。”
这话一出口,孙廉怔了一下,眉头拧得更紧:“为何?”
“他是太上皇之子,身份正统,论血脉比现在的陛下还正宗,你要说圣上信不过旁人,还能理解,可赵构?为何不能让他来办?”
秦喆盯着他看了几息,才压低声音开口:“你不在临安,不知道这些年宫里到底发生过多少事。
“我这次回岳州前,户部里几个老臣饭后闲聊,正说起圣上登基那会儿的旧事你知道赵构当时在干什么?”
“登基。”秦喆一字一顿,“他已经在筹办登基大典了。圣旨都起了草,据说连年号都想好了。”
孙廉面色微变:“可后来不是”
“对。后来宗老带着赵桓回来了。”秦喆压低声音,“京里有句话传得极快,说是一张脸,两副命。”
“朝中诸臣一看圣上,回来了,活的。谁还敢跟着赵构?”
“那场大典,一夜之间就散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你知道朝中这些年跟赵构走得近的是谁吗?”
“一个是李彦,一个是王黼。”
“前者已经被陛下定罪抄家,后者,坟头都平了。你再想想,陛下登基之后,整顿朝纲第一刀砍的是谁的人?”
孙廉缓缓点头,声音沉了下去:“是赵构。”
“所以你说,”秦喆目光直视他,“这样的一个人,圣上会把一件牵扯百万民命、数万亩土地、漕运要道的事交给他?”
“若换你是君王,会吗?”
孙廉喉结动了动,没说话。他当然不会。他太清楚权力这种东西,一旦出了宫门、落到对头手里,那就不是执行命令,而是另立山头。
“所以我说,孙兄,”秦喆语气不再含糊,“这事八成,是赵构自己借了圣上的名头。”
“他在岳州一步步做局,圈地、调人、弄商贾、建漕道,每一步都精得很。若不有人给他拦一拦,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这岳州还是不是岳州。”
“甚至——”他说到这儿,看了一眼四下,声音压得更低,“这是不是朝廷的地盘都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