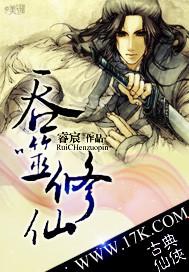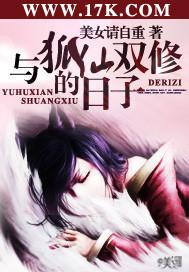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267章 回信与试探(第1页)
第267章 回信与试探(第1页)
仁忠没有犹豫:“大金如今虽强,但我西夏若真与其死绑,日后不过沦为其用兵之地。北则铁骑压境,南则百姓涂炭,哪边都不是活路。”
“如今大宋虽弱,然朝廷新立,君主锐意整军,边市通商之策,虽非久计,却是当下喘息良机。”
他顿了一顿,低声补了句:“我以为,须趁此时明投大宋,立稳立场,断大金之谋,护我西夏边疆与民生。”
李乾顺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起身踱到窗前,望着天色低沉的外城,神色沉思。
“濮王,你记得当年我父亲怎么说的?”
“西夏与辽、宋、金三国之间,谁也不是朋友,但谁也不能全得罪。”
“可现在不同了。”
他回头,目光极为清醒:“兀术这一手,不只是冲我西夏来的,是冲我们敢自立门户的心思。”
“再拖,只怕榷场之后,就是兰州、西宁、灵州一步步吞。”
仁忠躬身:“臣也正有此意。”
李乾顺沉声道:“传我口谕,命拓跋志坚即刻加固榷场驻防,增人、备马、重巡逻。”
“同时起草国书一封,向大宋君主陈述此事,言明我西夏愿共保边市安稳,互通声援,以求长久之势。”他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临安,乾清宫。
黄昏未至,殿中光线已有些黯。赵桓靠坐御案前,手中翻着一份由泾原军递来的急报,眉心微蹙,指尖在竹简边缘一下一下敲着,像是在理思绪。
殿中除了他,只有李纲一人。老臣立于案前,神色肃然,手负在身后,衣袍在夕光中晃得像一面沉稳的幡。
“陛下,榷场这事,虽未造成根本损害,但金人这手,是明摆着试探。”
“他们不敢直接开战,却想逼西夏自己退场。”
赵桓嗯了一声,视线落在文书末尾那段:“大金斥候第五营,斩首两人,活口三名。供称奉命扰乱边贸。”
“李相,你怎么看?”赵桓的声音平静,却透着一股试探意味。
李纲沉默了一下,才点头回道:“臣以为,金人此次动作虽小,但意图明显,正是试图搅乱西北边贸,逼西夏退缩。”
“他们现在不敢和咱们大宋撕破脸,只能玩这套暗地下刀的老把戏。”
“可问题是”他目光沉了几分,“西夏那边到底扛不扛得住,还得看他们的胆子。”
赵桓嗯了一声,随手将竹简卷起,靠坐在御案上,目光望向窗外微沉的天色。
“所以眼下咱不动。”他说得缓,却极有分寸,“兵不动,心也不能露。”
“我不想现在就跟金人摊牌,南线才刚稳,东南商号才归拢,岳州那边的事情还在收尾。此时一动,就把我半壁局面打乱了。”
李纲点头:“陛下思虑周全。”
“那西夏的态度呢?”赵桓忽然问。
李纲略一思索:“若他们真铁了心要跟咱联手,金人这一击反而是送了把火,点燃他们自己。”
“濮王仁忠一向主张亲宋,此番若能压过朝中旧派,站出来表态,那这事儿就能往下落子了。”
赵桓微微一笑,眼底光芒转瞬即逝。
濮王仁忠这个人他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