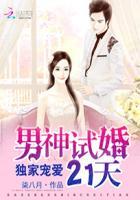趣书网>男主秦思齐 > 第46章 同窗追上(第2页)
第46章 同窗追上(第2页)
"谁让人家有真才实学呢?听说在甲班都有排名了。
"
"那又如何?
"赵明远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我爹说了,科举不光靠学问,还得有人脉。等明年我爹捐个监生名额
"林静之皱眉打断他:
"慎言。书院最忌讳这等言论。
"
角落里,张成默默收拾着书本。听到赵明远的话,他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笑,对这些富家子弟来说,科举之路有无数捷径可走;而像他这样的寒门学子,只能靠拼命苦读。
"张成。
"郑夫子突然叫住他,
"你留下。
"
等其他学子离开,郑夫子从案几底下取出一本手抄本:
"这是秦思齐当初的《孟子》笔记,你拿去看看。
"
张成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张成抱着笔记在雨中疾走。回到租住的小院,那夜,张成在油灯下逐字逐句研读秦思齐的笔记。那些批注不仅引经据典,还常常有独到见解。最让他震惊的是空白处密密麻麻的心得,有些想法很是新奇。
转眼到了第一次月考。乙班学子个个如临大敌,就连一向吊儿郎当的赵明远也熬夜学习,只想快点升到甲班。考场依旧设在明德堂,题目
"鱼与熊掌
"章,结合朱子集注写一篇义理文。
赵明远,李文焕奋笔疾书,林静之从容不迫,张成也写得飞快。下午放榜时,乙班二十四名学子中,仅有十二人得甲。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林静之、李文焕这两个公认的才子外,赵明远,张成也名列其中。按照书院新规,年过十四未能升入甲班者将被直接劝退;十四岁以下者则要与新生一起重读。而能入江汉书院的学子,哪个不是自幼熟读四书?竞争之残酷,可见一斑。
接下来的日子里,乙班的气氛越发紧张。郑夫子变本加厉,几乎每堂课都要拿秦思齐说事。那些被反复提及的
"秦思齐七岁就能如何如何
",像一道道枷锁,压得学子们喘不过气来。
十月的第二次月考,题目更加刁钻。不仅要考《论语》全篇
"颜渊问仁
"章,还要模拟朝廷写一篇《请赈两湖水患疏》。这种实用文体,若非家学渊源,普通学子根本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