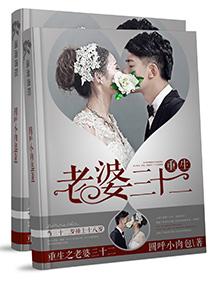趣书网>男主秦思齐 > 第54章 静水深流(第3页)
第54章 静水深流(第3页)
"齐哥儿后日要去考县试了。
"
祠堂内顿时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
"大安肯定得跟着去。
"秦茂山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
"再抽两个年轻力壮的后生护送。
"说着指了指身后的粗瓷大碗,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
铜板落入碗中的叮当声此起彼伏。碎银,铜钱,落在碗里,这是他们去年的收成。当秦思文和秦丰田的名字被喊出时,两个年轻后生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像两株新抽穗的高粱般精神抖擞。
更深露重,秦思齐推开窗户透气。清冷的月光下,祠堂的方向依然亮着灯火。他并不知道,此刻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正摸黑翻找着藏在炕洞里的钱串子,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那些积攒的铜板。
书案上的文章刚写到
"民为邦本
"四个字,墨迹尚未干透。远处传来守夜人悠长的梆子声,他想起离书院时夫子的谆谆教诲:
"科场文章贵在气韵,气从何来?从黎民百姓中来。
"
笔锋再次落下时,力道几乎要透纸背。窗外,启明星已经悄悄爬上了东边的山脊,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天刚蒙蒙亮,刘氏就开始在灶间忙碌。铁锅里煮着新碾的米粥,旁边的小灶上炖着昨晚就准备好的腊肉。她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生怕惊扰了还在熟睡的儿子。
"娘,您起这么早做甚?
"秦思齐披衣站在门口,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
刘氏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给你准备些干粮带着。听说县试要考一整天,可不能饿着肚子。
"她掀开蒸笼,里面是连夜赶制的糯米糕,
"这些耐放,你带着路上吃。
"秦思齐没有纠正母亲,只是一一答应。
院门外,秦思文和秦丰田已经早早候着。两人都换上了干净的衣裳,腰间别着防身的短棍。秦丰田手里还捧着个油纸包:
"我娘让带的咸菜,说是路上就着干粮吃。
"
日上三竿时,全村人都聚集在村口。秦茂山将凑来的银钱仔细包好。秦思齐拜别乡亲!
当送行的队伍终于启程时,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一辆牛车上,坐着四人,秦思文好奇的询问着齐哥儿府城里和书院的事。他回复着府城里的故事,头抬着一直望着村口,母亲没有离去,依然站在村口,单薄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那么瘦小而后消失在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