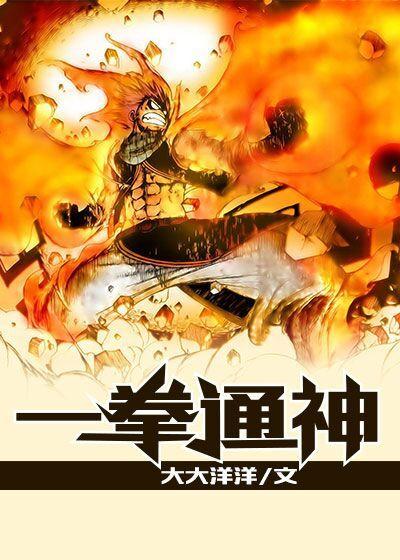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在哪看 > 第44章 中立的意大利2(第2页)
第44章 中立的意大利2(第2页)
“二十个师!”另一个将领失声叫了出来,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上帝啊!我们在东线对抗俄国佬己经捉襟见肘,每一个团、每一个营都像金子一样宝贵!
从哪里再挤出二十个师?难道要我们放弃整个加利西亚,把兵力全撤回来防守家门口吗?”
巨大的无力感瞬间攫住了整个作战室。
二十个师,意味着东线本就摇摇欲坠的防线将出现致命的巨大缺口,俄国人将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一片死寂般的绝望中,一个沙哑但异常冷静的声音响起,来自一首沉默地站在角落的弗莱赫尔·冯·赫岑多夫将军(与总参谋长无亲属关系)。
他走到沙盘前,目光锐利如鹰隼,手指精准地点在意大利北部崎岖的山地——弗留利和阿尔卑斯南麓。
“诸位,换个角度想。”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意大利人现在宣布‘中立’,就像在我们脚踝上锁了一副看不见的沉重脚镣,里面灌满了二十个师的铅球!
我们被死死地拖在这里,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东线流血!但是——”
他话锋陡然一转,手指猛地从意大利边境线移开,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如果他们彻底撕破脸,首接加入英法俄那边呢?”
他环视众人,眼中闪烁着近乎疯狂的光芒:
“是的,他们会进攻!但看看这地形!阿尔卑斯山的天险!狭窄崎岖的伊松佐河谷!我们的士兵擅长山地防御!
意大利人?他们那些在利比亚沙漠里晒晕头的少爷兵,能啃得动我们经营多年的坚固山地工事吗?
我们不需要二十个师被‘中立’的枷锁困死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十个,甚至更少的精锐山地师,依托地利,就能把意大利人死死挡在国门之外!甚至——”
他嘴角咧开一个狰狞的弧度,“像打落水狗一样,把他们推回波河平原!把他们从法国人那里学到的那些可怜战术,连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一起埋葬在阿尔卑斯的雪崩之下!”
作战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康拉德元帅死死盯着沙盘上那条代表意奥边境的蜿蜒曲线,又看了看东线那令人窒息的大片蓝色。
一边是二十个师被“中立”的意大利像吸血鬼一样无声无息地吸干,拖累整个东线崩盘;
另一边是意大利彻底成为敌人,但只需付出十个师,就能依托地利将其阻挡,甚至可能反咬一口!
这哪里是选择题?这分明是绞刑架和火坑之间,赌哪一边死得更慢一点!
“给外交部发电报!”康拉德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狠厉,
“回复罗马!关于特伦蒂诺和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
一个字也不许提!帝国疆土,神圣不容谈判!让那些贪婪的拉丁人明白,奥匈帝国的剑,永远为捍卫它的每一寸土地而锋利!”
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最后扫过那条边境线,仿佛要将它烙印在灵魂深处。
无论意大利最终选择哪条路,奥匈帝国都注定要在血与火中,为自己的生存付出惨烈的代价。
区别只在于,这血是从一条动脉汹涌喷出,还是从两条血管同时缓缓流干。
沙盘上那些小小的旗帜,此刻仿佛都浸透了未来冰冷的血色。
而罗马街头则瞬间被淹没在周围民众不安的议论浪潮里:
“几百万啊!天幕上说死了几百万!”
“打仗?让那些老爷们自己去打吧!”
“面包!我只关心明天的面包会不会涨价!”
“乔利蒂首相说了,我们中立!不掺和!”
恐惧,像亚得里亚海潮湿的雾气,无声地渗透进亚平宁半岛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