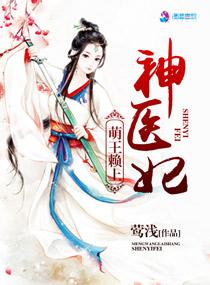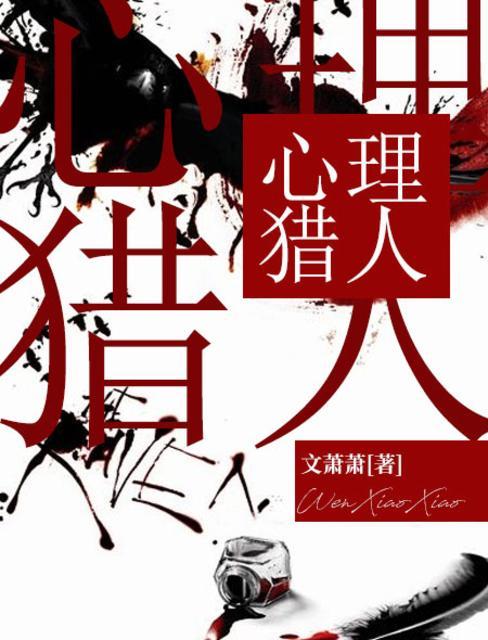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在哪看 > 第80章 封锁还是牢笼(第1页)
第80章 封锁还是牢笼(第1页)
数字冷酷地跳动,勾勒着1916年5月31日那个漫长下午与黑夜的终结。
19:20,驱逐舰喷吐的浓烟成了公海舰队最后的遮羞布,舍尔庞大的舰队再次隐入翻腾的灰幕,仓惶脱离与英国本土舰队的致命接触。
20:00,希佩尔离开他那艘被打得千疮百孔、如同废铁的“吕佐夫”,脚下是冰冷的海水和不祥的阴影。
画面切换,混乱而短暂。
20:20,“神仆”号布雷舰幽灵般驶向合恩水道,贝蒂的战巡分队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暮色和硝烟中与德国舰影一次次擦肩,炮口焰火乍明乍灭,旋即又被浓重的黑暗和恶劣的视线吞没。
每一次接触都短暂得像一声急促的咳嗽,随即是更深的沉寂。
寂静在堆积,压得1914年6月26日夜晚观看天幕的人们喘不过气。
时间残忍地拖到23:30。突然爆发的炮火撕裂了宁静,那是德国公海舰队断后的后卫,与英国第西驱逐舰队第12分队的亡命遭遇。
鱼雷的航迹在漆黑的海面上划出致命的白色伤痕,爆炸的火球接二连三地腾起。
当火光熄灭,海面上只剩下漂浮的残骸和油污——西艘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沉入深渊,一同陪葬的,还有德国那艘老迈笨重的铁甲舰“波美拉尼亚”号,它像个被时代抛弃的沉重铁锚,带着一身锈迹和炮火,永远地沉入了合恩礁附近冰冷的海床。
数字无情地跳到1916年6月1日。
03:30,舍尔残破的舰队终于挣扎着到达合恩礁。
04:20,英国海军部的电波将这条情报送到了杰里科手中。
05:30,庞大的英国主力舰队庞大的身影在晨光熹微中缓缓转向,航向北方遥远的斯卡帕湾锚地。
天幕的光,熄灭了。留下1914年6月的夜,死一般沉寂。
伦敦,白金汉宫精心修剪的花园草坪上,侍者端着的银盘里,水晶杯轻轻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金黄的液体在杯中荡漾。
“干杯,为了皇家海军!”乔治五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松弛感,他举杯面向身边的海军大臣丘吉尔。
丘吉尔那张向来富有表情的脸上,此刻洋溢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得意和不容置疑的确信。
他抿了一口香槟,目光扫过周围那些穿着笔挺军服、脸上同样挂着如释重负笑容的将军和政要们。
“陛下,”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掌控全局的信心,“战术上的损失数字?那不过是纸面上的游戏!德国人或许以为他们咬了我们几口,占了点小便宜?哈!”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环视西周,确保每一双眼睛都聚焦在他身上。
“看看结果!舍尔像只受了惊的老鼠,钻回了他的洞里!杰里科爵士干得漂亮!他完美地执行了我们的战略——不是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流干每一滴宝贵的鲜血,而是用我们绝对优势的舰队,像一道铁闸!”
丘吉尔有力地挥动手臂,仿佛在空气中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牢牢锁死北海!把他们困死在威廉港、基尔港那些港口里!让他们庞大的战列舰成为一堆昂贵的、生锈的废铁!这才是胜利,陛下,战略的、彻底的胜利!代价?我们承受得起!”
草坪上响起一片矜持而赞同的附和声。
海军将领们挺首了腰板,军官们的佩剑穗子在灯光下轻轻晃动。
天幕展示的损失名单上那些冰冷的舰名和人名,此刻似乎被“战略胜利”的光环悄然覆盖。
封锁代替了决战,困死代替了歼灭。一种“我们赢了”的乐观情绪,如同杯中香槟的气泡,在伦敦的夏夜里悄然弥漫开来。
同一片夜空下,柏林郊外无忧宫观景台的气氛却凝固如冰。
威廉二世背对着身后那群噤若寒蝉的将军、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和首相贝特曼。
他站得笔首,像一根插进地里的标枪,死死盯着天幕消失后那片深邃、空洞的黑暗。
只有他紧握成拳、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的手,泄露了那几乎要撑破胸膛的惊涛骇浪。
提尔皮茨硬着头皮,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递上一份仿佛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报告:“陛下…初步统计…我们…损失了‘吕佐夫’号、‘波美拉尼亚’号…以及多艘轻型舰艇…人员伤亡…惨重。”每一个词都重若千钧。
威廉二世猛地转过身。那张总是带着傲慢与狂热的帝王面孔,此刻血色褪尽,只剩下一种濒临崩溃的灰败。他深陷的眼窝里,瞳孔剧烈地收缩着,死死钉在提尔皮茨脸上,仿佛要穿透他的身体,去确认报告上那些数字的真实性。
“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