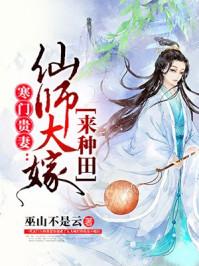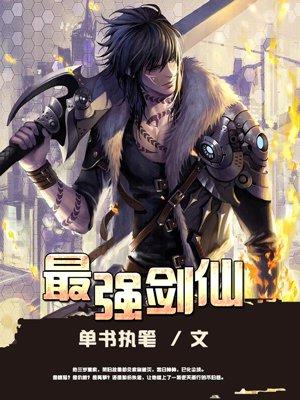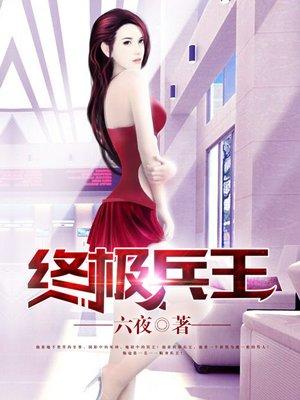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09章 演员演绎术文公第六年(第2页)
第109章 演员演绎术文公第六年(第2页)
宋代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阶层崛起,促使瓦舍勾栏成为表演艺术的新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内的瓦舍多达五十余座,其中大小勾栏终年上演杂剧、傀儡戏、影戏、诸宫调等表演。杂剧作为宋代戏剧的代表,角色行当发展为“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的“五花爨弄”体系,表演融合唱念做打,情节更为丰富,如《目连救母》杂剧,以曲折故事与精彩演绎,将宗教题材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诸宫调则突破单一曲调限制,以多种宫调联套演唱长篇故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通过说唱结合的方式,细腻刻画人物情感,推动了叙事性表演艺术的成熟。
与此同时,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辽代的“臻蓬蓬歌”,以热烈欢快的节奏展现契丹民族的豪迈风情;金代院本继承宋杂剧风格,进一步增强了喜剧色彩与讽刺意味,为元杂剧的兴盛奠定基础。蒙古铁骑统一中原后,元杂剧迎来黄金时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剧作家辈出,《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等经典剧目层出不穷。元杂剧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固定结构,以曲牌联套演唱,角色分工细化为旦、末、净、杂,演员通过程式化表演塑造鲜明人物形象,使中国戏曲艺术首次形成完整的表演体系。
此外,元代的散曲演唱、蒙古族的长调短调、藏族的藏戏等表演形式也各放异彩。长调以悠扬辽阔的旋律诉说草原生活,藏戏则通过面具、歌舞和说唱演绎佛教故事与历史传说。这一时期,表演艺术的受众从宫廷贵族扩展到广大市民与少数民族群体,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创新达到新高度,不仅深刻影响了明清戏曲的发展,更在世界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生动写照。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演员演绎迎来了更为成熟与多元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盛,推动戏曲艺术走向鼎盛,形成了“诸腔竞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明代中叶,传奇剧崛起,取代了元杂剧的主导地位。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以浪漫主义笔触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传奇剧推向艺术巅峰。在表演上,传奇剧突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局限,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均可演唱,角色塑造更为立体。同时,昆山腔经魏良辅改良后,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特色脱颖而出,成为“百戏之祖”。梁辰鱼的《浣纱记》作为第一部用改良后的昆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将昆腔搬上舞台,其细腻的身段、优雅的唱腔与精美的服饰,构建起独特的东方美学范式,对后世戏曲表演的程式化、规范化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随着地方戏的勃兴,形成了“花雅之争”的格局。“雅部”昆曲以其高雅的艺术格调占据宫廷与文人阶层;“花部”则包括梆子腔、皮黄腔等地方剧种,以通俗易懂的唱词、激昂热烈的曲调深受市民喜爱。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融合汉调、秦腔等声腔,逐渐演变出京剧这一集大成的剧种。京剧在表演上讲究“唱念做打”四功与“手眼身法步”五法,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各有严格表演规范,如梅兰芳饰演旦角时,通过精妙的水袖动作与眼神流转,将古典女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谭鑫培以醇厚嗓音与细腻身段,开创“谭派”老生表演艺术。此外,清代宫廷设立南府(后改升平署),集中全国优秀艺人,编排《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等连台本戏,推动戏曲表演向规模化、精细化发展。
除戏曲外,明清时期的说唱艺术也达到新高度。北方的鼓词、子弟书,南方的弹词、道情等形式多样,如苏州弹词以“说、噱、弹、唱”为特色,艺人凭借一把三弦、一面琵琶,便能演绎长篇故事,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白妞王小玉说唱技艺的描写,生动展现了其艺术感染力。同时,木偶戏、皮影戏等民间表演形式也更加成熟,操纵者通过精巧技艺赋予木偶、皮影鲜活生命,成为百姓重要的娱乐方式。明清时期的演员演绎,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构建起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完备体系,对东亚乃至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历剧烈震荡,表演艺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列强入侵带来的文化碰撞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促使演员演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态势。
戏曲领域,京剧虽仍占据主流地位,但开始融入时代精神。汪笑侬等艺人将改良思想注入表演,他改编的《党人碑》《哭祖庙》等剧目,借古讽今,呼吁救亡,开创“汪派”京剧的革新风格。随着新式剧场的出现,上海的“新舞台”率先引入转台、灯光等西方舞台技术,打破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布景模式,为观众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同时,地方戏在改良运动中焕发新生,川剧“三庆会”倡导戏曲改良,强调“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粤剧艺人马师曾、薛觉先吸收西方话剧元素,革新表演程式,形成“薛腔”“马腔”等流派。
话剧作为舶来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采用分幕表演、生活化对白等现代戏剧形式,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回国后,他们在上海等地的演出引发轰动,推动了文明戏的发展。欧阳予倩、田汉等先驱者,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民族审美相结合,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等作品,以犀利笔触批判封建礼教,展现社会现实,演员们摒弃戏曲程式化表演,注重内心体验与真实情感表达,开创了中国现代表演艺术的先河。
电影表演也在这一时期悄然萌芽。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京剧短片《定军山》,成为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开启了戏曲与电影结合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明星影片公司等相继成立,电影表演逐渐从戏曲化走向生活化。阮玲玉在《神女》中细腻刻画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通过微表情与肢体语言传递复杂情感;赵丹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中塑造的市井青年形象,以自然灵动的表演风格,成为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的典范。
此外,传统说唱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北方大鼓艺人骆玉笙创立“骆派”京韵大鼓,以韵味醇厚的唱腔演绎《剑阁闻铃》等曲目;苏州评弹艺人严雪亭革新表演形式,融入时事新闻,使传统艺术更贴近民众生活。鸦片战争后的表演艺术,在守正与创新中不断突破,既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又吸纳现代艺术养分,为中国表演艺术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演员演绎领域的认识,便已展现出惊人的理论深度与艺术自觉。古希腊戏剧诞生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祀仪式,演员们戴着夸张的面具、穿着高底靴,在半圆形剧场中通过程式化的动作与吟诵式对白,将神话故事与哲学思考搬上舞台。面具不仅是身份标识,更赋予演员超越个体的象征意义,使他们能够化身为神只、英雄或凡人,完成从“自我”到“角色”的神圣转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演员需通过“摹仿”(mimesis)展现行动与情感,其对悲剧“卡塔西斯”(净化)功能的论述,将表演提升至伦理与哲学高度,认为演员的演绎能够引发观众的恐惧与怜悯,进而实现精神的升华。
古罗马时期,戏剧逐渐从宗教仪式转向世俗娱乐。演员地位虽较为低下,却发展出精湛的技艺。哑剧(pantomimus)成为主流表演形式,演员无需台词,仅凭肢体语言与表情变化诠释复杂故事,这种表演对身体控制与情感传递的极致要求,催生出一批以细腻表演着称的艺术家。塞内加的悲剧作品中,对角色内心冲突的深度刻画,也促使演员探索更具层次感的表演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剧场建筑的声学设计与宏大空间,倒逼演员通过夸张的形体动作和洪亮的声音,确保表演的感染力能够覆盖全场观众,这种空间与表演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了西方戏剧的表演美学。
这一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剧作家与诗人,如柏拉图、贺拉斯等,虽对表演艺术持有不同态度(柏拉图甚至将演员逐出理想国),但他们的论述共同构建了西方表演理论的基石。无论是对“摹仿”本质的探讨,还是对演员与观众情感共鸣机制的思考,都为后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等现代表演理论的诞生埋下伏笔,使欧洲表演艺术从源头上便具备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并重的特质。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表演艺术的发展因基督教的统治与社会动荡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宗教成为艺术创作与演绎的核心主导,戏剧几乎完全服务于宗教传播,神秘剧、奇迹剧和道德剧成为主流形式。演员们大多由神职人员或教众担任,他们在教堂或街头搭建的临时舞台上,通过简化的表演重现圣经故事、圣徒事迹或宣扬道德训诫。角色塑造被严格限定在宗教教义框架内,演员需以肃穆、虔诚的姿态演绎神圣人物,夸张的面具与肢体动作被收敛,取而代之的是程式化的手势和诵经般的念白,表演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敬畏神灵、净化灵魂。
随着城市经济的复苏与行会组织的兴起,戏剧逐渐走出教堂,走向世俗。行会成员开始参与戏剧创作与表演,在市集、广场等公共场所上演世俗化的戏剧作品。这一时期的演员开始尝试脱离宗教表演的刻板模式,为角色注入更多人性色彩。例如在道德剧中,代表“贪婪”“懒惰”等抽象概念的角色,演员通过幽默诙谐的肢体语言和对白,使说教内容更易被民众接受。尽管演员社会地位依旧低微,常被视为“游荡者”而受到世俗法律限制,但他们通过流动演出,促进了不同地区表演风格的交流融合。
在理论层面,中世纪学者对表演的探讨多依附于神学与修辞学。他们强调戏剧的教化功能,将演员的演绎视为传递宗教真理的工具,甚少关注艺术本体的审美价值。然而,这种对表演“功能性”的极致追求,客观上推动了舞台叙事结构的发展——为了清晰传达教义,戏剧逐渐形成线性叙事、角色类型化等特征,为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复兴积累了实践经验。中世纪的表演艺术虽在宗教枷锁下发展缓慢,却如同蛰伏的种子,在等待思想解放的春风拂过,重新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于演员演绎观念的研究应用与实践发展,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
在古印度,《舞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戏剧理论着作,构建起极为系统的表演美学体系。它将表演归纳为“四肢表演”“语言表演”“内心表演”和“眼神表演”四大类,提出“味论”(Rasa)与“情论”(bhava)学说,认为演员需通过肢体、表情、声音的精准配合,唤起观众心中“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等八种审美体验。印度古典戏剧如卡塔卡利舞剧,演员以夸张的脸谱、繁复的手势(手印)和程式化的舞步诠释角色,男性演员甚至可反串女性角色,通过细腻的眼神流转与肢体韵律,将神话传说中的神灵与英雄演绎得栩栩如生。婆罗多舞剧则更注重舞者与音乐、诗歌的配合,舞者通过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转身,将史诗故事娓娓道来,这种表演强调“内在情感的外在投射”,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阿拉伯世界的表演艺术在伊斯兰文化的浸润下独具特色。由于伊斯兰教对偶像崇拜的禁忌,表演多以说唱艺术、皮影戏(卡拉格兹)和诗歌吟诵的形式呈现。中世纪阿拉伯的“卡瓦力”(qawwali)音乐表演,歌手通过激昂的歌声与即兴创作的歌词,传递对神灵的赞颂与对生命的感悟,其充满张力的声音表达与肢体律动,能够引领观众进入宗教迷狂状态。而在皮影戏中,艺人通过操纵牛皮雕刻的人偶,配合极具感染力的旁白与配乐,演绎《一千零一夜》等民间故事,人偶的动作设计既保留程式化特征,又充满灵动变化,展现出阿拉伯艺术家对叙事性表演的独特理解。此外,阿拉伯学者如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在哲学着作中探讨情感与表达的关系,间接影响了表演中对情绪传递的重视。
在非洲大陆,部落文化中的仪式性表演是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面具舞在西非、中非广泛流传,舞者佩戴雕刻精美的面具,模仿祖先、动物或自然神灵的姿态,通过激烈的舞蹈与鼓点节奏,沟通人神两界。面具不仅是身份象征,更是表演的核心媒介,如科特迪瓦的丹族面具舞,舞者通过快速旋转、跳跃和夸张的肢体扭曲,展现原始生命力;东非的斯瓦希里说唱艺术,艺人以押韵的诗句配合复杂的节奏,讲述历史传说与生活智慧,表演时的语调变化、身体摆动与观众互动,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这些表演形式虽未形成系统理论,但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对角色塑造、情感表达的理解代代相传,体现出人类表演艺术的多元智慧。
而在美洲大陆,原住民的表演艺术同样以独特的方式与自然、神灵和历史对话。在玛雅文明中,祭祀仪式上的舞蹈表演被视为与神明沟通的神圣途径。舞者身着缀满羽毛、贝壳的华丽服饰,模仿美洲豹、蜂鸟等图腾动物的动作,在金字塔前的广场上,配合低沉的陶笛与击鼓声,演绎创世神话与农耕历法。玛雅彩陶与壁画上刻画的舞者姿态,展现出对肢体语言的高度提炼,其夸张的肢体延展与定格造型,不仅传递着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更承载着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
阿兹特克文明的表演艺术则充满了悲壮的史诗色彩。每逢重大节庆,祭司与战士会化身为羽蛇神魁札尔科亚特尔、战神维齐洛波奇特利等神只,通过持续数小时的仪式性舞蹈,重现部落迁徙与战争历史。舞者佩戴镶嵌绿松石的面具与皮质铠甲,以极具张力的步伐与呐喊,模拟战斗场景,将尚武精神与宗教信仰熔铸于表演之中。这些表演往往伴随着复杂的祭坛仪式,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严格遵循古老的程式,被认为能够影响神灵对人间的庇佑。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太阳舞”堪称表演艺术的集大成者。舞者围绕神圣的太阳舞杆,以鹰羽头饰与鹿皮长袍为装扮,通过循环往复的旋转与吟唱,表达对自然馈赠的感恩。表演中,领舞者的动作会根据季节、狩猎成果等现实需求进行即兴调整,既保持传统框架,又融入当下的生活祈愿。此外,因纽特人在冰原上的喉音歌唱表演,两位女性通过快速交替的喉音颤动与面部表情变化,模拟风声、动物鸣叫,在极简的形式中展现出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表演无需复杂的道具与服饰,仅依靠纯粹的声音与身体语言,传递出极地民族对生存环境的深刻理解。美洲原住民的表演艺术,以与自然、信仰紧密相连的独特形态,构建起人类表演艺术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彰显着新大陆文明对艺术表达的深刻思考与创新实践。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同样在演员演绎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在日本,能剧与狂言作为古典戏剧的双璧,深刻诠释了东方表演美学的精髓。能剧起源于平安时代的祭神仪式,演员头戴雕刻细腻的面具,身着华丽的十二单衣或甲胄,以缓慢、庄重的程式化动作演绎神佛、幽灵、武士等角色。面具在能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一面具在不同角度的光影下,能呈现出喜怒哀乐的微妙变化,演员通过微不可察的头部倾斜、指尖颤动与抑扬顿挫的念白,将角色的幽玄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狂言,则以诙谐幽默的风格见长,演员无需面具,通过夸张的表情与滑稽的肢体语言,讽刺贵族与僧侣的愚蠢,其即兴发挥与生活化的对白,展现出民间表演艺术的鲜活生命力。此外,歌舞伎作为江户时代兴起的市民艺术,男扮女装的“女形”演员以妖冶的妆容、华丽的服饰与极具张力的舞台动作,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其旋转、定格的“见立ち”表演手法,既强调戏剧性又充满视觉冲击力。
朝鲜半岛的传统表演艺术同样独具魅力。盘索里作为说唱艺术的代表,一人分饰多角,通过激昂的唱腔、丰富的方言与夸张的肢体动作,讲述《春香传》《沈清传》等长篇叙事诗。说唱者仅凭一把扇子与鼓板,便能模拟风雨声、马蹄声,乃至不同人物的对话与情感,展现出惊人的表演功力。假面舞剧“傩戏”则通过夸张的木雕面具与诙谐的舞蹈,讽刺两班贵族的虚伪,演员们踏着轻快的节奏,以戏谑的肢体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兼具娱乐性与批判性。此外,朝鲜王朝宫廷中的“处容舞”“剑舞”等表演,舞者身着传统服饰,动作刚柔并济,将礼仪规范与艺术美感完美融合,彰显出东方舞蹈的典雅气质。
在东欧的俄罗斯,尽管中世纪的东正教曾严格限制戏剧表演,但民间的游吟诗人“史诗歌手”(斯科里克)以说唱形式传承着《伊戈尔远征记》等英雄史诗。他们手持古斯里琴,用充满激情的嗓音与手势,生动再现战争场面与英雄壮举。18世纪,随着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俄罗斯引入欧洲戏剧形式,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表演体系。到了20世纪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体验派”表演理论,强调演员需“从自我出发”,通过“心理技术”深入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以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打动观众,这一理论不仅革新了俄罗斯的表演艺术,更对全球现代戏剧与电影表演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俄罗斯民间的假面哑剧、木偶戏等传统表演形式,也以丰富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东欧地区表演艺术的多元魅力。
在东南亚地区,对于演员演绎,宗教信仰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催生出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艺术形式。印度教与佛教的深远影响,使戏剧表演常与祭祀仪式紧密相连,舞者与演员通过精心雕琢的肢体语言和极具象征意义的装扮,传递神圣故事与哲学思想。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巴龙舞堪称文化瑰宝。表演中,舞者佩戴巨大的巴龙(善神象征)与兰达(恶神象征)面具,以夸张的头部摆动、灵动的身躯扭转,配合甘美兰乐队极具节奏的打击乐,演绎善恶永恒争斗的神话故事。舞者肌肉的细微颤动与面具下流转的眼神,将角色的神性与魔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爪哇岛的哇扬皮影戏同样别具一格,艺人们操纵着精心雕刻的牛皮人偶,在油灯投射下于白色幕布上演英雄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操纵者不仅要熟练控制人偶完成复杂动作,还需模仿不同角色的声音,配合甘美兰音乐进行即兴说唱,展现出超凡的表演技艺与文化底蕴。
泰国的孔剧(Khon)以其华丽的宫廷风格闻名,演员身着缀满金饰的丝绸服饰,头戴精美的尖顶面具,通过严格规范的手势(拉玛手势)、舞步与眼神配合,演绎罗摩王子的传奇故事。表演中,每个动作都蕴含特定含义,如手部兰花指造型象征优雅,急促的小碎步代表焦急,演员需经过多年训练才能精准诠释角色。与之相对,老挝的水上木偶戏则更贴近民间生活,艺人在湄公河畔的水面上操纵木偶,配合传统乐器演奏与民谣吟唱,展现农耕、捕鱼等日常生活场景,木偶灵活的关节设计使其能完成划船、撒网等逼真动作,充满生活情趣。
柬埔寨的罗摩皮影戏,曾是吴哥王朝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牛皮皮影雕刻精细,人物形象具有典型高棉艺术风格。演出时,艺人将皮影贴近油灯幕布,通过巧妙的光影变化与娴熟的操控,使皮影在幕布上呈现出千军万马奔腾、神魔激烈交战的宏大场面。而缅甸的木偶戏则融合了戏剧、舞蹈与杂技元素,木偶通过复杂的线控装置,能完成跪拜、舞蹈、持物等精细动作,操纵者往往藏身幕后,仅凭声音与精湛技艺赋予木偶鲜活生命,讲述佛本生故事与民间传说。这些东南亚的表演艺术,既是宗教信仰的具象表达,也是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展现出演员演绎在多元文明中绽放的独特光彩。
随后,当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科学大发展、启蒙运动,乃至是后来改变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和在历史上极具重大影响力的战役与关键历史事件,面对新兴生产力与制度体系的“冲击”与“影响”,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在由原先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摸索、建立、发展与成熟阶段,直至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在演员演绎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突破。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掀起对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复兴热潮,演员们摆脱中世纪宗教戏剧的刻板束缚,开始追求对人性的真实表达。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登上舞台,演员们通过细腻的情感演绎,将哈姆雷特的忧郁、麦克白的野心等复杂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打破了角色塑造的程式化藩篱。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提出“严肃剧”概念,倡导演员以理性控制情感,通过精准的表演技巧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这种理论为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美学标准。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深刻改变了表演的呈现方式。电灯的发明让舞台告别油灯与煤气灯,实现了精准的光影控制;留声机和电影技术的诞生,使表演突破时空限制得以永久保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世纪末创立的“体验派”表演体系,强调演员要“从自我出发”,深入体验角色内心世界,通过“心理技术”实现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一理论不仅革新了俄罗斯戏剧,更成为现代表演艺术的基石。而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通过理性的表演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为表演艺术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