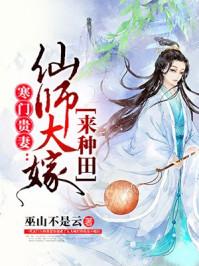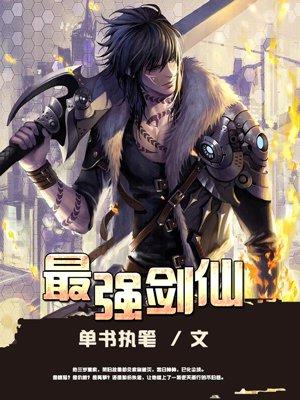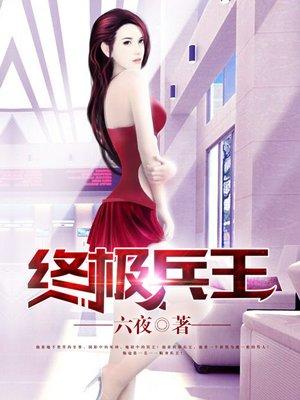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09章 演员演绎术文公第六年(第1页)
第109章 演员演绎术文公第六年(第1页)
从亘古蛮荒到现代文明,从东方华夏大地到西方艺术殿堂,无论是粉墨登场演绎人间百态的戏曲名伶、用高亢歌喉诠释戏剧张力的歌剧艺术家,还是活跃于大小银幕塑造鲜活角色的专业演员,从本质上而言,他们都是人类情感的摆渡者与时代记忆的镌刻者。这些艺术从业者以血肉之躯为载体,将抽象的情绪转化为具象的表演符号,用肢体语言与声音韵律搭建起跨越时空的情感桥梁。
而他们所表现和演绎的内容,恰似一面多棱镜,既折射着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又投射出人类精神世界的浩瀚星空。这些被精心雕琢的艺术作品,或是复刻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时刻,或是虚构充满哲思的幻想故事,每一个角色、每一段剧情都承载着创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的思考,成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情感共鸣的媒介。
至于演员的职业素养与表演技术,无疑是决定艺术呈现质量的关键要素。扎实的台词功底、精准的肢体控制、细腻的情绪表达,如同精密仪器的各个部件,唯有完美配合,才能让表演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同时,职业操守中的敬业精神、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与共情能力,更是支撑演员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的精神支柱。
从概念定义上来讲,演员是通过专业训练掌握表演技巧,以塑造角色为职业的艺术工作者。但这简短的定义背后,实则蕴含着复杂的艺术创作过程——他们需要打破自我与角色的界限,在现实与虚构间自由穿梭,用专业能力赋予文字生命力,让平面的剧本蜕变为立体鲜活的艺术形象。
当我们从深层内核与内涵研究时,我们对此也能够发现,演员的表演本质上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探索与呈现。每一次角色塑造,都是对不同人生境遇的体验与诠释,既是对社会现象的微观剖析,也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宏观思考。这种艺术实践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审美体验,更推动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艺术大师,他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巧层面,将表演升华为一种哲学表达。从古希腊戏剧家通过悲剧探讨命运与人性,到梅兰芳以水袖勾勒东方美学意境,再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体系化表演理论,这些大师们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深邃的思想内涵,不断拓宽着表演艺术的边界,让这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始终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光芒。
至于古今中外圣贤高人,对此的评价往往直指表演艺术的灵魂深处。孔子观“八佾舞于庭”,以礼乐之仪教化人心,将戏剧雏形纳入“仁”与“礼”的哲学体系,认为艺术表演是道德与审美交融的载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辩证演员的模仿本质,既警惕其对真实理念的偏离,又认可戏剧净化情感的社会功用。东方禅宗以“身如傀儡,心若明镜”喻表演,强调演员需以空灵心境映照角色;西方尼采借酒神精神赞美戏剧狂欢,视其为人类超越理性、回归生命本真的通道。这些跨越时空的思索,将表演艺术从技艺层面提升至精神对话的高度。
而当我们尝试深入理解,便会发现表演艺术如同流动的文化基因,始终与人类文明同频共振。在敦煌壁画的乐舞图卷里,在莎士比亚剧作的诗性独白中,在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气节里,表演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延续。它像一面魔镜,既让观众在他人故事中照见自我,也促使创作者在角色塑造中完成对人性的追问。当演员在舞台或镜头前完成一次呼吸、一个眼神的传递,本质上都是在构建跨越时代的精神对话,让古老的智慧与当下的困惑在此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让表演艺术真正成为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永恒火炬。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各大题材戏曲戏剧与话剧,还是后来的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视听艺术作品,通过演员们的精湛演绎,成为历史与现实的生动注脚。这些优秀作品不仅能重现往昔岁月,引发观众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情感共鸣,更以艺术的笔触歌颂人类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它们敢于直面社会阴暗面,以辛辣的讽刺揭露现实问题,同时也在战争、天灾人祸等重大命题中,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与光辉。在传承与反思的基础上,创作者们不断开拓创新,打造全新题材,让作品成为传递正确价值观与时代正能量的精神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而在这之中,如何演出真情实感与新鲜感,能够激发民众百姓的共鸣,还有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激流,创作出更多创新作品,想来从古至今,无论是优伶、伶人,梨园子弟、倡优、俳优,希波克拉底斯与话剧演员,还有其他各大类型的演员,还是近现代的电影电视剧演员,这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功,同时也是急需掌握的重要技能与能力。
至于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智者圣贤和历史学者,对此的记录,恰似为艺术长河镌刻下永恒的坐标。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以细腻笔触记载优孟衣冠讽谏楚庄王的轶事,不仅展现了古代俳优“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表演智慧,更揭示了表演艺术“以戏载道”的社会功能;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演员对情感的摹仿提升至哲学高度,认为其通过净化(卡塔西斯)作用,能引导观众完成精神层面的升华。这些记载不仅是对表演艺术价值的肯定,更蕴含着对演员技艺的深刻洞察。
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出“机趣”之说,强调演员需以灵动表演唤醒文本生命力;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更系统阐述“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理念,指出演员需在程式化表演中注入个人体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提出“要使自然更自然”的表演准则,与中国古代“以形写神”的表演美学遥相呼应。这些跨越时空的理论探索,共同勾勒出表演艺术的本质追求——在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寻找情感表达的最佳平衡点。正如清代名伶程长庚“一字一泪,感人至深”的表演,或是当代演员通过细腻诠释让经典角色焕发新生,历史的记载既是对过往艺术成就的致敬,也为后世演员提供了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让表演艺术在代代传承中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而当我们揭开历史长河长卷,回望古今,想必对此也有更有感悟。
对于演员演绎这方面的学问,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原始部落社会,先民们已在祭祀仪式与庆典活动中,通过模仿狩猎场景、自然现象的肢体语言和原始歌舞,尝试用表演传递对世界的认知与祈愿。彼时的岩画与彩陶纹饰中,那些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正是人类最早的表演雏形,他们以简单夸张的动作和呼喊,将集体记忆与生存经验融入艺术表达。古埃及神庙壁画上记载的宗教仪式戏剧,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吟诵传唱,都证明表演自诞生起,便承载着沟通天地、凝聚族群的重要使命。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孕育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同时期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址的洞穴岩壁画、石制玉制乃至早期青铜金属工具器皿,还有其他手工艺品中,对于演员演绎领域的认识,我们也会发现,那些质朴而生动的艺术符号,正是人类表演意识觉醒的珍贵物证。仰韶彩陶上舞蹈纹盆中牵手共舞的原始先民,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群体表演的韵律感,仿佛能听见远古的鼓点在陶器表面震颤;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巫师祭祀场景,通过人物夸张的肢体姿态与神秘的图腾纹样,展现出仪式表演中人与神灵对话的庄严氛围。
在两河流域,乌尔王陵出土的里拉琴共鸣箱上镶嵌的战争与庆典场景,以贝壳与青金石拼贴出演员般鲜活的人物动态;古印度河谷文明遗址中的滑石印章,刻画着舞者扭转腰肢的灵动造型,暗示着舞蹈表演在早期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遗存,虽非现代意义上的表演记录,却以具象化的艺术语言,揭示出人类自蒙昧时期便试图通过肢体、声音与仪式,将内心世界外化为可感知的艺术表达。它们不仅是原始表演形态的物质载体,更折射出早期人类对情感传递、故事讲述和集体认同的永恒追求,为后世表演艺术的蓬勃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火种。
紧接着,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工具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当人类社会逐渐脱离野蛮时代,逐步朝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时,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于演员演绎方面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认知内容的价值体现,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并且,无论是对于历史的生动再现,还是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二次升华创造,在演员演绎方面,也是出现了近乎专业化的“雏形”,并在后来不断朝着体系化、多元化、完善化,以及成熟化方向发展。
在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乐”已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周礼》中记载的“大司乐”一职,专门掌管宫廷乐舞教育与祭祀表演,要求舞者依“六代乐舞”的严格规范,通过“文舞”执龠翟、“武舞”持干戚的程式化动作,展现王朝威仪与道德教化。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舞”字,形如人执牛尾而舞,印证了祭祀舞蹈在沟通天地中的神圣地位。至春秋战国,俳优群体突破礼乐桎梏,以滑稽戏仿和讽喻表演干预政治,如优旃“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的荒诞谏言,开创了表演艺术“以戏议政”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激荡为表演艺术注入了思辨的灵魂。儒家以“礼崩乐坏”为忧,孔子修订《乐经》,强调“乐者,通伦理者也”,将表演视为道德教化的载体;墨家则批判统治者“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的奢靡,主张“非乐”以节俭用度,不同学派的论争推动了表演功能与价值的深度探讨。这一时期,民间“乡饮酒礼”中的乐舞表演,以“金声玉振”的和谐韵律强化宗族纽带;而楚辞的诞生,更使诗歌与表演紧密结合,屈原《九歌》中“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的描写,生动展现巫觋装扮神灵歌舞娱神的场景,为后世戏曲的角色扮演提供了原始范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的表演开始注重情感表达与角色塑造。《史记》记载齐国俳优淳于髡以“滑稽多辩”之姿,通过模拟不同人物的言行,在讽谏中巧妙传递治国理念,其“隐语”技巧已初具表演艺术的叙事性与代入感。同时,各国贵族豢养的倡优群体,将音乐、舞蹈、杂技熔于一炉,如赵国倡女郑旦在宴席间“扬袂鄣日而舞”的场景,既展现高超技艺,也成为贵族阶层文化消费的象征。这些实践不仅打破了表演的阶层壁垒,更催生出对表演理论的初步探索——庄子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为后世表演中“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埋下伏笔,使表演艺术从单纯的仪式行为,逐步迈向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精神创造。
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为表演艺术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乐府”机构的设立,不仅广采民歌、整理乐舞,更将表演艺术推向规模化与专业化。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异域的音乐、舞蹈、杂技如箜篌演奏、胡旋舞、幻术表演等纷纷传入中原,与本土艺术交融碰撞,催生出气势恢宏的“百戏”艺术。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河南南阳汉画像砖上,倒立、走索等百戏场景栩栩如生,展现出汉代表演艺术“总揽天人,包举万类”的磅礴气象。
这一时期,角抵戏从单纯的武术竞技演变为带有故事情节的表演形式。《西京杂记》记载的《东海黄公》,演员需装扮成黄公与白虎,通过程式化的打斗与念白,演绎人与兽的生死较量,这被视为中国戏剧表演中“故事扮演”的重要开端。同时,说唱艺术在民间蓬勃兴起,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唱俑,袒胸露腹、手舞足蹈的夸张造型,生动再现了当时艺人以诙谐语言和丰富表情逗乐观众的场景。
在宫廷表演领域,“相和歌”“鼓吹乐”等音乐形式与舞蹈紧密结合,形成“歌舞戏”雏形。汉乐府诗《陌上桑》《木兰诗》等文学作品,经乐工改编为歌舞表演后,不仅使诗歌得以更广泛传播,也推动了表演艺术叙事性的增强。到了东汉时期,洛阳的宫廷宴乐规模更盛,据《后汉书》记载,每年元旦举行的“元会仪”上,除延续百戏表演外,还融入了“鱼龙曼延”等大型幻术场景——艺人操控着巨大的彩扎巨兽,忽而化作比目鱼喷吐水雾,忽而幻化为身长八丈的黄龙腾跃而起,配合着铿锵的鼓乐与杂技演员的高难度动作,令观者如临其境。此外,东汉王朝与西域、东南亚诸国往来频繁,安息(今伊朗)、掸国(今缅甸)等遣使进贡时,常带来异域乐舞,如安息的“五弦琵琶”演奏、掸国的“幻术吐火”,宫廷专门设立“黄门鼓吹署”吸纳融合这些外来技艺,编排成彰显国力的“四夷乐舞”,于重大庆典中展示。表演艺术由此成为彰显国威、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秦汉时期的表演艺术,在融合与创新中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后世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时局与频繁的民族迁徙,却意外成为表演艺术交融创新的催化剂。政权更迭与南北分野,促使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相互碰撞:北方游牧民族刚健质朴的歌舞,如鲜卑族的“马上乐”,与南方细腻婉转的吴歌、西曲交汇融合,形成“清商乐”这一兼具南北风情的音乐表演体系。同时,佛教的广泛传播深刻影响表演形态,寺院中的“行像”活动以戏剧化方式演绎佛经故事,僧人们装扮成佛陀、菩萨、恶鬼等角色,通过夸张的妆容与肢体动作,将晦涩教义转化为通俗表演,推动了宗教剧的萌芽。
这一时期,参军戏在俳优表演的基础上发展成熟。其固定角色“参军”与“苍鹘”通过滑稽问答、相互戏谑的形式讽喻时政,如后赵石勒时期,怜人因参军贪污而设角色戏弄,开后世戏曲角色互动之先河。此外,《兰陵王入阵曲》的诞生堪称表演艺术的里程碑,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因貌美不足以威敌,遂戴面具、着铠甲,以舞蹈模拟战斗场景,将士们配以悲壮战歌,这种将音乐、舞蹈、故事与角色装扮融为一体的表演,已具备戏剧的基本要素,被后世视为戏曲雏形。
在理论层面,嵇康《声无哀乐论》对音乐与情感关系的探讨,为表演艺术注入哲学思辨;谢赫在《画品》中提出的“六法”,其中“气韵生动”“应物象形”等理念,间接影响了表演中对形神关系的追求。而北魏时期石窟壁画中大量伎乐飞天形象,敦煌莫高窟251窟的反弹琵琶乐伎、云冈石窟的伎乐雕刻,不仅是艺术瑰宝,更直观展现了当时乐舞表演的服饰、道具与动作特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演艺术在乱世中突破地域与文化界限,完成了从散点式娱乐向体系化艺术的重要过渡,为隋唐时期的艺术鼎盛积蓄了磅礴力量。
而在隋唐时期,大一统帝国的辉煌气象为表演艺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将其推向了巅峰。随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宫廷对表演艺术的投入与重视达到空前高度,教坊与梨园两大专业机构的设立,标志着表演艺术迈入系统化、专业化发展阶段。教坊负责管理俗乐,汇聚各地民间艺人,编排适合宫廷宴乐的歌舞节目;梨园则由唐玄宗亲自督教,专注于法曲创作与器乐演奏,培养出李龟年等一批技艺精湛的表演艺术家。
这一时期,音乐、舞蹈、戏剧深度融合,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艺术形式。《霓裳羽衣曲》作为盛唐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将西域《婆罗门曲》与中原清商乐完美融合,杨贵妃以轻盈飘逸的舞姿演绎“飘飖似仙子”的意境,配合三百乐工的协奏,展现出“仙乐风飘处处闻”的华美场景。同时,以《踏谣娘》为代表的歌舞戏,突破了单纯歌舞的表现形式。剧中,演员分别饰演苏郎中与妻子,通过唱念做打和诙谐表演,讲述夫妻间的故事,既有悲剧色彩,又不乏喜剧效果,其角色分工与情节设置,已具备成熟戏剧的雏形。
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也让表演艺术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音乐舞蹈大量传入,胡琴、琵琶等乐器广泛应用,胡旋舞、胡腾舞风靡长安,白居易曾以“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描绘舞者的灵动身姿。在民间,瓦舍勾栏中的百戏表演精彩纷呈,幻术、杂技、说唱等艺术形式争奇斗艳,吸引着不同阶层的观众。而佛教变文的流行,僧人以说唱结合的方式讲述佛经故事,推动了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为后世的话本、小说奠定了基础。
在理论与创作方面,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形成,系统规范了音乐调式与演奏技法;王昌龄、皎然等文人对诗歌意境的探讨,也影响了表演艺术中情感表达与审美追求。隋唐时期的表演艺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创新精神,构建起庞大而完备的艺术体系,不仅成为当时文化繁荣的象征,更对东亚乃至世界表演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的成熟树立了典范。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尽管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但表演艺术在夹缝中依然顽强生长,并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宫廷表演因王朝的兴衰更迭而规模缩减,然而割据政权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反而促使表演艺术走向多元化与个性化。南唐后主李煜不仅在诗词创作上造诣非凡,其宫廷中盛行的歌舞表演,融合江南婉约风情与道教神话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致的舞台呈现,成为乱世中的一抹艺术亮色;前蜀王建墓出土的二十四伎乐石刻,生动再现了宫廷宴乐中器乐演奏的场景,箜篌、羯鼓、横笛等乐器一应俱全,展现出当时高超的音乐表演水准。
在民间,表演艺术打破了宫廷的桎梏,更加贴近市井生活。随着城市经济的局部繁荣,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虽不及隋唐时期兴盛,却依然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舞台。民间说唱艺术在此期间进一步发展,“说话”(讲故事)、“鼓子词”等形式开始流行,艺人们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蓝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吸引听众,为后来宋代话本的成熟奠定基础。此外,参军戏在民间继续传承演变,角色类型更加丰富,表演内容也从讽喻时政逐渐转向对市井百态的刻画,增强了喜剧效果与娱乐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文人与艺人互动频繁,许多文人因仕途失意投身艺术创作,为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如后蜀欧阳炯所作的《花间集序》,虽为词集序文,却暗含对音乐歌舞艺术的审美见解;而文人创作的诗词也常被改编为曲词进行演唱,促进了文学与表演艺术的深度融合。尽管五代十国的表演艺术难以再现隋唐时期的宏大辉煌,但它以灵活多样的姿态扎根民间,在传承中孕育新变,为宋代表演艺术的全面繁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表演艺术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频繁的文化交融,为表演艺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其在碰撞与融合中实现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