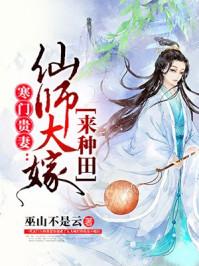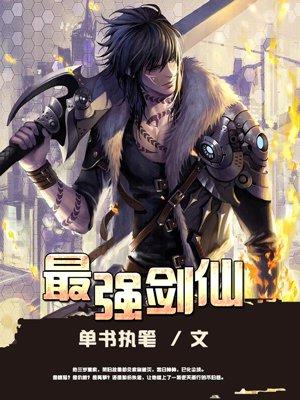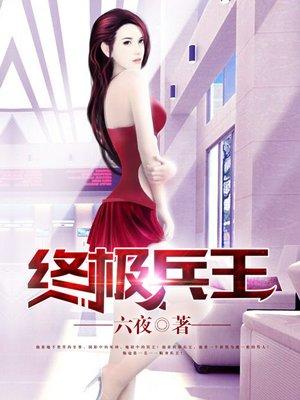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11章 关税进出策文公第八年(第1页)
第111章 关税进出策文公第八年(第1页)
关税与货物进出口政策作为贯穿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经济制度,自丝绸之路驼铃悠扬的商贸往来起,便以独特的经济杠杆属性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从秦汉时期"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通商政策,到威尼斯共和国凭借海上关税体系崛起为地中海贸易霸主;从明代隆庆开关掀起的白银货币化浪潮,到1840年鸦片战争背后的贸易壁垒冲突,这些政策始终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代,关税协定谈判桌前的博弈、自贸区政策的创新实践,更成为各国经济实力角逐的重要战场。
这一领域交织着复杂的经济逻辑与鲜活的历史故事,既孕育出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经典案例,也催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事件。东印度公司凭借垄断性贸易特权建立的殖民经济体系,北美十三州因《糖税法》引发的独立战争,以及近代中国被迫签订的"协定关税"不平等条约,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推动了经济理论的迭代发展,更成为塑造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注脚。而某些国家在特殊时期实施的奇葩关税政策,如中世纪欧洲对胡须征税,也是成为一大特色亮点。
至于古今中外的着名教育家和思想领域大师,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自由放任、取消贸易限制",以及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的"保护性关税是培育民族工业的重要手段"这些经典论述一般,他们对关税与进出口政策的探讨从未停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便从城邦治理角度思考贸易管控对社会稳定的意义;中国古代管仲提出"关市讥而不征"的宽松政策,主张通过轻税促进商品流通以实现富国强兵;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则系统论证了贸易顺差与关税保护的关联性,为早期殖民国家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近代以来,大卫·李嘉图以"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理论基石,凯恩斯则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必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关税在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中的作用;而当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关税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保护意义。这些思想者从哲学思辨、经济规律、社会伦理等不同维度切入,既有对市场机制的深刻洞察,也包含对国家利益、民生福祉的现实考量,其观点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理解贸易政策演变的思想图谱,至今仍为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启示。
与此同时,无论是从古希腊学者色诺芬论述的"商业税收理论",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倡导的自由贸易学说;从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到凯恩斯主义对关税保护政策的辩证思考,不同时代的思想巨匠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理论印记。正如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所言:"关税是一国工业的保姆",这些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不仅构建起完备的经济理论体系,更为当代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着持续的智慧启迪。在数字贸易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今天,关税政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仍在持续演进,不断续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关税和货物进出口政策,从概念定义上来讲,是国家基于主权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所征收的流转税,以及为调节贸易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行政性规范。在国际通行准则中,关税被明确界定为“海关根据国家制订公布的海关税则,对进出其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而进出口政策则涵盖了从关税税率设定、贸易配额管理到海关监管措施等系统性规则。这些看似清晰的条文,构成了国际贸易秩序的基本框架,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工具。
然而,当我们尝试从深层次领域研究分析,同时从不同角度着手探究其深层关键内涵价值,我们便会发现,这些政策绝非简单的经济工具。在经济学维度,它们是调节供需平衡的杠杆,通过关税壁垒或优惠税率影响商品价格,进而重塑全球产业链布局;在政治学层面,关税与进出口政策是国家主权的具象化表达,承载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资源供应的重要使命,甚至成为外交博弈的有力筹码;从社会学视角审视,这些政策直接关联民生福祉,既能通过保护政策维系传统产业就业,也可能因贸易摩擦引发物价波动,影响社会稳定。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浪潮冲击下,关税的征收对象正从实体货物向数据跨境流动延伸,进出口政策的内涵也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不断迭代,其背后折射出的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的碰撞,正推动着世界贸易规则体系的深刻变革。
这种变革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中显得尤为突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关税谈判曾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新型自贸协定的兴起,正重塑着关税减让的路径与规则。这些协定不仅在传统货物贸易关税议题上寻求突破,更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纳入政策协调范畴,形成了“边境后规则”的全新竞争维度。例如,cptpp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倒逼成员国在投资准入、监管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关税政策已不再是孤立的经济条款,而是成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试金石。
在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双重压力下,关税政策还衍生出了新的战略功能。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碳排放纳入关税征收考量,表面是环境治理手段,实则构建起绿色贸易壁垒,试图通过碳关税规则掌握全球气候经济话语权;而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本质上是以技术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将关税工具与产业政策深度捆绑,形成技术封锁的“政策组合拳”。这些新动向表明,关税与进出口政策正从单纯的贸易调控工具,演变为服务国家战略、参与规则制定的复合型政策体系。
展望未来,随着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渗透,全球贸易形态将进一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虚拟商品的跨境交易如何征税、数据要素的流动如何监管、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属如何界定,这些全新课题对现有关税与进出口政策体系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在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进中,共同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的贸易治理新范式,而这也将成为关税与进出口政策书写新篇章的重要方向。
当我们回望人类社会漫长发展演进史,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在关税和货物进出口方面,其实在全球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交融史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与很高的地位。同时,关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如同历史长河中的涟漪,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博弈、经济格局与文化碰撞。从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关市之征”,到威尼斯商人跨越地中海时缴纳的过境税;从大航海时代各国为争夺贸易霸权设立的保护性关税,到近代以来因工业革命催生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始终是国家利益与全球协作的平衡点。它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文明对话的隐形纽带——茶叶、丝绸、香料等商品的流通,伴随着生产技术、艺术风格、宗教信仰的传播,在收税与通关的流程中,不同地域的智慧与创造力得以交汇,最终塑造出今日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图景。而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关税制度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跨境电商、虚拟商品的兴起,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规则,这或许将开启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全新篇章。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原始部落社会,人类就已出现了简单的物品交换与“关税”雏形。当不同部落带着陶器、兽皮、谷物等特色物产进行交易时,某些占据交通要道的部落便会收取一定比例的实物作为“通行费”或“保护费”,这可以看作是关税的原始形态。这些早期的“关税”虽然没有成文规定,却在无形中规范着部落间的经济往来,保障着交易秩序。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孕育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同时期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址的洞穴岩壁画、石制玉制乃至早期青铜金属工具器皿,还有其他手工艺品中,对于关税与货物贸易进出口领域的认识,我们也会发现,这些古老文明早已通过器物特征暗示着贸易的存在。良渚文化出土的精美玉器,其材质多非本地所产,证明了跨地域资源交换的频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海贝,更指向了与沿海部落的物物交易。这些文化遗存中,部分器物的形制、纹饰在不同地域呈现相似性,如仰韶彩陶与西亚彩陶的螺旋纹图案,不仅反映出文化传播路径,也暗示着贸易路线上可能存在的“税收节点”——掌握稀有资源或先进工艺的部落,或许通过控制贸易通道获取额外物资,以维持其在区域交换网络中的优势地位。而古埃及陶罐上的运输船队浮雕、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中记载的商队货物清单,则以更具象的方式揭示:早在文字成熟初期,人类就开始用符号记录交易规则与物资分配,这些原始的“关税档案”,为后世理解早期文明的经济秩序提供了珍贵线索。
紧接着,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工具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当人类社会逐渐脱离野蛮时代,逐步朝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时,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于关税贸易和货物进出口方面的认识,相比于先前,也是随之产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认知内容的“再现”与“重现”,以及探讨其背后的“人文内涵”和金融贸易专业领域“理论原则”及“方式策略方法”,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并且,无论是从过去历史借鉴分析,还是当下具体的现实条件来分析制定相应的关税和货物贸易进出口等政策,也是出现了近乎专业化的“雏形”,并在后来不断朝着体系化、多元化、完善化,以及成熟化和纵深化,还有大众化和灵活化方向发展。
在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关市之征”已从原始的实物交换规则演变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周礼·地官》详细记载了司关、司市等官职的设立,专门负责检查货物、征收关税,其中“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的规定,更体现出关税政策与社会治理的联动性。西周时期,设于交通要道的“津关”不仅对往来货物征税,还承担着查验违禁品、保障国家安全的职能,玉璧、青铜器等贵重物品的流通,必须持有官府颁发的“节传”方可通关。与此同时,青铜铭文如《兮甲盘》记载了周王对南淮夷地区的贸易指令,要求其定期进贡布帛、粮食,并规范了关市税率,这些文字成为研究早期关税制度的珍贵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经济变革的浪潮,将关税制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各诸侯国为增强国力、扩充财源,纷纷重视关市税收,关税政策开始与军事、外交战略紧密交织。齐国在管仲的改革下,推行“关市几而不征”的政策,降低关税壁垒,吸引各国商贾汇聚临淄,使齐国凭借商业繁荣成为春秋首霸;而秦国商鞅变法时,通过“重关市之赋”抑制商业发展,将资源集中于农业与军事,为秦国崛起奠定经济基础。《管子·海王》中提出“官山海”理论,主张国家控制盐铁等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以关税调节资源分配,这种宏观调控思想影响深远。
此时的关税征收体系更趋精细,《礼记·王制》记载“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除经济职能外,关税关卡还承担着文化审查与边境管控功能。郑国商人弦高以牛犒劳秦军的典故,侧面反映出商人在国家外交中的特殊作用,也凸显出关税在保障战略物资流通方面的重要性。此外,《商君书》《韩非子》等着作中关于“利出于一孔”“重农抑商”的论述,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关税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而《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吕不韦等大商人的跨国贸易活动,则生动展现了当时关税制度下的商业生态。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关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诸侯博弈的重要筹码,也为后世封建王朝的经济治理提供了丰富经验。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促使关税制度迎来规范化与规模化的革新。秦朝统一六国后,凭借“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将分散的关隘整合为覆盖全国的贸易网络,在函谷关、武关等战略要地设关征税,以“关市律”明确税率与通关流程,严厉打击走私行为。出土的云梦秦简中,详细记载了对私运盐铁、皮革等物资的惩处条例,体现出秦朝通过关税强化中央集权的决心。
汉朝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关税的功能与影响力。汉武帝时期,为筹措对匈奴作战的军费,推行“算缗”“告缗”政策,对商人的货物、车船等征税,同时垄断盐铁专卖,将关税与专营制度结合。张骞凿空西域后,丝绸之路的开辟让关税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枢纽,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记录了西域商队携带香料、皮毛通关纳税的详细信息;而长安、洛阳等城市设立的“市令”机构,不仅管理国内贸易,还对胡商货物征收“市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交融。
在理论层面,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强调重农,但桑弘羊主持的盐铁会议中,围绕“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展开的辩论,实质上探讨了关税在调控经济、平衡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汉书·食货志》系统记载了汉代的财政制度,其中关税收入占比显着,成为支撑帝国扩张与文化传播的经济支柱。无论是西域驼队络绎不绝的商贸往来,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秦汉时期的关税制度,既保障了王朝的经济安全,也成为中华文明辐射周边、联通世界的重要桥梁。
随后,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南北分裂对峙的局势,使关税制度呈现出多元且灵活的特点。各政权为维持割据势力与军事开支,纷纷在交通要道与长江、黄河等水运枢纽设关征税。曹魏政权在许昌、洛阳等地设立“津关都尉”,严格管控盐铁、战马等战略物资的流通,对过往商队征收实物税,以保障军需;孙吴凭借长江天险,在濡须坞、石头城等沿江要塞设卡,对珍珠、香料等海外贸易货物课以重税,充盈的关税收入支撑起其强大的水师力量。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番禺(今广州)、建康(今南京)等港口城市兴起,关税制度随之革新。朝廷设立“市舶司”雏形机构,专门管理进出口贸易,对外国商船运来的象牙、犀角等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实行“官市”制度,优先收购珍稀物资。《南史》记载,刘宋时期仅广州一地的关税收入,就足以支撑岭南地区的军政开支。同时,各政权为吸引流民与商客,常出台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如南齐曾短暂取消部分内陆关卡征税,促进了区域间物资流通。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积极学习汉制,将游牧民族的贸易传统与中原关税制度融合。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在长安设立“互市”,对西域商人携带的货物征收货币税,推动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复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在洛阳设“四通市”,对南北贸易货物征税,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这一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关税制度在适应复杂政治格局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为隋唐时期关税制度的再度整合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在隋唐时期,国家再次走向大一统,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促使关税制度迎来全面革新与鼎盛发展。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后,隋文帝杨坚下令减免关市之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极大刺激了商业活力,使洛阳、长安等都市迅速成为国际商贸中心。隋炀帝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水路关税成为新的增长点,在运河沿线的汴州、扬州等城市设立关卡,对漕运货物按品类分级征税,形成了贯通南北的水上贸易税收网络。
唐朝建立后,关税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关市令”的成文法典,详细规定了关税征收标准、违禁物品清单及通关流程。在陆上,唐朝控制丝绸之路东段,于敦煌、龟兹等地设关,对往来商队征收“过所税”,并发放“过所”(通行证)保障贸易安全;在海上,武则天时期正式设立市舶司于广州,专职管理海外贸易,对阿拉伯、波斯商船运来的香料、珠宝等货物,按“舶脚”(入口税)、“抽分”(实物税)、“收市”(官营优先采购)三重体系征税。《唐六典》记载,广州一地市舶收入每年可达数百万贯,支撑起唐朝的海上霸权与文化辐射力。
这一时期,关税不仅是财政支柱,更成为文化交融的催化剂。长安西市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汇聚了粟特、大食等各国商人,关税政策的宽松吸引了大量外来文化,胡服、胡乐、佛教艺术借由商路传入中原;而唐朝的丝绸、瓷器、造纸术也通过贸易网络传播至中亚、欧洲。同时,陆羽《茶经》中对茶叶贸易的记载,以及杜佑《通典》中关于“关市之税,轻重有恒”的经济论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化了对关税功能的认知。隋唐关税制度以其开放性与规范性,既巩固了盛世根基,也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关键纽带。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政权割据、山河破碎的局面使得关税制度陷入混乱与变革并存的特殊状态。各政权为维持割据势力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纷纷在辖境内外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关税征收呈现出随意性与多样性交织的特征。后梁在汴河沿岸增设关卡,对过往商船课以重税,甚至出现“一物过一税”的现象,以填补连年征战带来的财政缺口;南唐则凭借长江天险,在金陵、扬州等商贸重镇设立“都商税务司”,对丝绸、茶叶等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对进口的海外香料、珠宝实行“博买”制度,由官府垄断经营,将关税与专营收益合二为一,支撑起南唐相对繁荣的文化艺术。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关税政策朝令夕改。前蜀王建为吸引商贾,曾短暂推行轻税政策,降低川蜀地区关卡税率,使成都成为西南地区商贸中心;而后蜀孟昶时期,为应对后周军事威胁,大幅提高过境税,甚至对民间日用品也征税,导致商路阻滞、民生凋敝。在北方,契丹政权控制燕云十六州后,在边境设立“榷场”,与中原政权开展互市贸易,对输出的马匹、皮革和输入的茶叶、布帛分别征税,这种特殊的关税模式既满足了契丹对中原物资的需求,也成为其渗透中原经济的手段。
尽管时局动荡,关税制度仍在夹缝中发展。部分政权开始尝试规范税收流程,如吴越国制定《市舶条法》,对海外贸易货物的征税标准、检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保障了杭州、明州等港口的贸易秩序。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关税乱象的反映,韦庄在诗作中描述商贾因高额关税被迫改道的困境,而陶岳《荆湖近事》则记载了湖南马氏政权利用湘江水运关税富国强兵的举措。这些实践与记录表明,五代十国时期的关税制度虽受战乱冲击,却在混乱中孕育着新的变革因子,为宋代关税体系的成熟积累了经验。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元政权的并立与疆域的空前拓展,促使关税制度在碰撞与融合中实现重大突破。北宋建立后,为解决“三冗”问题,将关税视为财政收入的核心支柱,不仅在汴河、运河沿线密集设置税务机构,对国内商品流通实施“住税”(交易税)与“过税”(流通税)双重征收,还进一步完善市舶司制度。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的市舶司下设“抽解”“博买”“禁榷”等细则,对进口货物按种类分级征税,香料、象牙等奢侈品税率高达十分之一,同时官府优先收购贵重物资,市舶收入一度占朝廷财政的20%。《宋会要辑稿》详细记载了市舶司对外国商船的勘验、抽税流程,体现出宋代关税管理的精细化。
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政权,同样构建起特色鲜明的关税体系。辽朝在边境设立“榷场”,与宋、西夏开展官方贸易,对输出的羊马、皮毛征收实物税,输入的茶叶、丝绸则以铜钱计税,形成以物易物与货币征税并行的模式;西夏凭借丝绸之路灵州段的控制权,对往来商队征收“过路费”,并在与宋的互市中对青盐出口实行专营,以关税强化经济独立性。金朝占据中原后,继承宋辽制度,在黄河、淮河沿线设关,对南北物资流通课税,同时在山东半岛设立市舶司,恢复海上贸易征税,《金史·食货志》记载其关税收入支撑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军事开支。
元朝实现大一统后,推行“重商”政策,关税制度呈现国际化特征。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庆元等港口实施“官本船”制度,官府出资造船并提供资本,与商人按比例分利,同时降低市舶税率至十五分之一,吸引阿拉伯、欧洲商船纷至沓来。陆上丝绸之路方面,元朝在驿站体系基础上设卡征税,对欧亚商队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大都繁华市集,正是低关税政策下东西方贸易繁荣的写照。此外,元朝首次将纸币“交钞”用于关税结算,推动了金融与贸易的深度融合,为后世关税货币化提供了范例。这一时期,各政权通过关税制度的创新,既满足了财政需求,也促进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深度交融。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全球贸易格局的剧变,中国关税制度在传统框架下经历深刻变革,并在近代化浪潮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政策,将市舶司纳入礼部管辖,以“怀柔远人”为宗旨,对朝贡使团携带货物给予免税优待,甚至以高于市价回赐,实则将关税作为政治外交的工具。但民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促使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在月港设立督饷馆,实行“引税”(商船许可证费)、“水饷”(按船型征税)、“陆饷”(按货物征税)、“加增饷”(对日本贸易附加税)的复合税制,标志着官方开始承认并规范私人海外贸易。
清朝前期,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取代市舶司职能,对进出口货物制定详细税则。但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仅留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形成“保商制度”——由行商担保外商缴纳关税并管理其行为,关税收入虽稳却限制了贸易活力。此时,西方殖民势力已叩开中国大门,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鸦片走私扭转贸易逆差,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迫使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协定关税”条款,海关自主权丧失,进口税率被固定在5%左右,远低于西方各国。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引入近代海关管理制度,虽提升了关税效率,却使海关沦为列强经济侵略的工具。
在文化层面,明清小说如《喻世明言》中对商人跨国贸易的描写,以及《广东新语》对十三行贸易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关税对民间经济的影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海国图志》等着作,则开始反思传统关税政策的局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主张。明清关税制度的演变,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缩影,更成为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主权逐步丧失的历史见证,为后世理解全球化浪潮下的贸易主权问题提供了深刻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关税进出口和商品货物贸易领域的认知与认识,也是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脉络。古希腊城邦时代,商业贸易的繁荣促使关税制度初现雏形。雅典作为海上贸易中心,在比雷埃夫斯港设立了专门的税务机构,对进出口货物征收2%的关税,这一税率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标准化关税制度之一。税收不仅用于维持港口设施,还支撑起城邦的军事和文化建设,如雅典卫城的修建便得益于贸易税收的积累。各城邦间还通过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关税互惠政策,如雅典与米利都的盟约中就明确了双方商人在彼此港口的纳税标准,这种早期的“关税协定”为区域贸易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