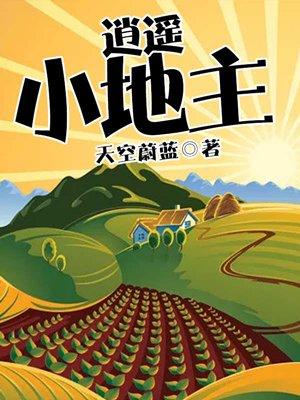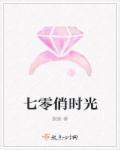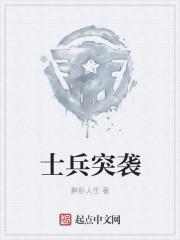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11章 关税进出策文公第八年(第3页)
第111章 关税进出策文公第八年(第3页)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商业纠纷,影射当时地中海贸易中关税壁垒、汇率波动对商人命运的左右;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描写主人公途经的村镇关卡,借骑士冒险故事展现封建领主割据下关税征收的混乱与荒诞。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关税制度对个体生活的冲击,更揭示了贸易规则背后的权力博弈与人性百态。
近代以来,文学艺术对关税议题的呈现更具批判性与现实意义。茅盾在《子夜》中,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外国资本的商业斗争,深刻展现晚清协定关税制度下,民族工业在洋货倾销与高关税压迫的双重困境中艰难求生的图景;老舍《骆驼祥子》里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间接反映了关税失衡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涌入城市的社会危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马孔多小镇从封闭到被外来商品冲击的过程,隐喻殖民时代关税政策对本土经济与文化的毁灭性影响。
在当代艺术领域,关税与贸易议题突破文字边界,以多元形式引发思考。装置艺术家通过模拟海关关卡、堆叠象征关税壁垒的集装箱,批判贸易保护主义;电影《中国合伙人》以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创业为背景,展现关税政策松绑如何激发个体经济活力;戏剧《丝路天歌》则以古丝绸之路为蓝本,通过舞台上的商队跋涉与关卡征税场景,重现关税在文明交流中的纽带作用。这些跨越时空的艺术创作,既留存了关税制度变迁的鲜活印记,也赋予经济史以人文温度,让后世得以在审美体验中触摸历史深处的贸易脉动。
话说,王嘉这小子,在这几天,其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也由原先那方面领域,向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关税进出口与商品货物贸易领域密切相关的着作典籍,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方面进行转变。
而他呢,也是在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在完成书库对应区域的部分竹简卷帛书籍的整理工作后的短暂休息中,开始暗暗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来。
王嘉倚着书库斑驳的木柱,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刚整理好的《管子》竹简。午后的阳光斜斜穿过窗棂,在堆积如山的简牍上投下细碎光影,恍惚间竟与昨日在《周礼》残卷里读到的“司关掌国货之节”字样重叠。他望着不远处正擦拭青铜书镇的师姐,突然想起她前日提及齐国“关市几而不征”时眼中的神采,喉头微动,终于忍不住开口:“师姐,您说管仲主张轻税通商,可若遇战事急需钱粮,又该如何权衡?”
这话惊动了正在整理《商君书》的大师兄,他放下手中竹简,棱角分明的脸上泛起思索:“秦国重关市之赋,倒是能迅速充盈国库。但《史记》载,商鞅变法后,连商旅携带的皮革都要课以重税,久而久之。。。。。。”话音未落,二师兄已从《韩非子》的简册中抬起头,折扇轻点案几:“这便要说到‘利出一孔’了!秦国将商贾之利收归国有,看似短利,实则为耕战立国扫平障碍。”
王嘉听得入神,忽觉后颈一凉——小师妹不知何时绕到他身后,正晃着新拓的《兮甲盘》铭文摹本:“你们莫要纸上谈兵!瞧瞧这西周铭文,玉帛通关需持‘节传’,关税早与邦交安危勾连。前日师父讲《左传》,弦高犒师那节,若不是郑国关卡早有预警。。。。。。”她清脆的声音在书库里激起阵阵回响,惊飞了梁间栖着的燕雀。
众人笑闹间,王嘉却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出了神。竹简上那些沉睡的文字,此刻仿佛化作千万商队,驮着丝绸、青铜与海盐,在函谷关的晨雾里、在淄水的波光中,踏着关税的鼓点,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娓娓道来。他摸了摸怀中新抄的《关市之征》札记,突然明白师父为何总说“典章即历史”——原来这横竖交错的竹简纹路里,藏着的不只是税则,更是整个春秋战国的呼吸。
之后不久,晨雾未散时,王嘉已蹲在书库西北角,借着天窗漏下的微光,指尖逐卷拂过蒙尘的竹简。当触到刻着《管子·海王》字样的简牍时,他的呼吸骤然一滞——前日与师兄师姐讨论的“官山海”理论,正是出自此处。他迅速抽出竹简,又从袖中掏出炭笔,在泛黄的绢帛上匆匆记下卷数与关键词,墨痕晕染间,仿佛看见千年前齐国街市上往来如织的商贾。
接下来的日子,书库成了王嘉的战场。每当整理到《商君书》残卷,他便用朱砂笔在争议处圈点;遇到《周礼·司关》的记载,就将竹简平摊在案,逐字比对不同版本的差异。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窗棂,在他膝头堆积的简册上投下斑驳光影,而他浑然不觉,只专注地用麻绳将相关典籍捆成一摞,发间还沾着掉落的竹简碎屑。
随着收集的资料渐丰,王嘉案头的札记已堆成小山。他将各国关税制度绘成图表,却在“秦国重税与齐国轻赋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卡了壳。竹简上“利出一孔”与“通货积财”的主张在脑海中反复冲撞,急得他深夜辗转难眠,索性披衣起身,就着油灯又翻出《史记·货殖列传》。烛火摇曳间,吕不韦跨国贸易的记载跃然纸上,却反而让他生出更多疑问。
第二日破晓,王嘉揣着沉甸甸的札记,先是堵住了正要去晨读的大师兄。两人站在廊下,就着青铜灯台展开辩论,唾沫星子溅在竹简上也浑然不觉。午后,他又追着二师姐到桑树林,听她援引《韩非子》解读关税与权术的关联,蝉鸣声中,他的笔记写得飞快,手腕都泛起了红痕。
暮色四合时,王嘉终于敲响了左丘明的房门。老先生拄着木杖,颤巍巍地展开他带来的竹简,浑浊的双目突然亮起:“来,看这《兮甲盘》铭文——”沙哑的声音在屋内回荡,烛光将师徒二人的身影投在墙上,时而因激烈的讨论而剧烈晃动。当王嘉捧着豁然开朗的札记退出房门时,月光已洒满庭院,竹影婆娑间,他忽然理解了师父常说的“读史如掘宝”。
此后旬日,王嘉带着竹简与地图踏上实地考察之路。他在渑池故道丈量古时关卡的间距,在临淄遗址摹写残存的市籍碑刻,甚至乔装成小商贩,跟着商队体验通关流程。当他亲眼见到黄河渡口的税吏核验“节传”,听着老船工讲述当年齐国商船云集的盛况,那些在竹简上冰冷的文字,终于化作鲜活的历史。
归程那日,王嘉站在山丘上眺望夕阳下的关隘。怀中札记已被汗水浸湿,却写满了全新的批注。山风卷起他的衣袂,恍惚间,他仿佛看见千年前的商队正驮着丝绸与青铜,沿着他脚下的古道,在关税的鼓点中走向远方。此刻,所有的疑惑都已化作胸中沟壑,那些曾困扰他的文字,终在日夜求索间连成了璀璨的星河。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文公第八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文公第八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文公第八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文公执政鲁国第八年的时候,和鲁文公先前执政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且“耐人寻味”的事情。
鲁文公八年春季,残冬的霜雪尚未褪尽,洛邑王城的宫墙已蒙上一层萧瑟。周襄王卧榻之侧,侍臣们屏声敛息,望着天子枯槁的面容——自去年秋染寒疾,龙体便每况愈下。檐角铜铃在朔风中轻响,惊起阶前觅食的寒鸦,却惊不散大殿深处弥漫的药味。此时各诸侯国的朝贡队伍正陆续抵京,宋使带来的杞梁酒、晋使进献的河曲马,都在阙外库房积成小山,却再无人有心思清点。太宰捧着新制的玉圭候在殿外,这是为春祭准备的礼器,可天子连起身祭天的气力都已耗尽。王城的漏壶滴着冰水,每一声都似敲在众臣心上:这维持了四十六年的天下共主之局,怕是要随这残冬一同去了。
洛阳城外的洛水初涨,蒹葭苍苍间,一支快马队冲破晨雾。为首的周室史官衣襟浸透汗水,怀中密函用天子玺印封着——襄王已于三月底薨逝,临终前遗命秘不发丧,待太子郑从郑国返京继位。消息如惊雷炸响各诸侯国:齐桓公霸业已逝,晋文公新丧未久,此刻周室大丧,恰是诸侯问鼎的微妙时机。鲁国朝堂上,鲁僖公摩挲着竹简上“王崩”二字,目光扫过阶下大夫公子遂——此人素与晋国交好,而此刻晋卿赵盾正权倾朝野。殿外蝉鸣渐起,檐角的铜铃却不再作响,仿佛连风都在屏息等待这场天下变局的开端。
当周襄王的梓宫终于从王城抬出时,洛邑已被连绵秋雨笼罩。棺木上覆盖的玄色锦缎浸了水,沉重得需二十四人共抬。送葬队伍行至成周城遗址,突然狂风大作,挽幛被卷上半空,露出棺木缝隙中渗出的暗红汁液——那是天子临终前咳血的痕迹。随葬的青铜礼器在雨中泛着冷光,其中一尊鼎内尚残留着未燃尽的艾草,这是太医最后为天子驱寒的偏方。送葬的庶民中有人低泣,更多人则望着东方——那里,晋使的快马正驰向鲁国,而宋都商丘的城门下,一场诛杀即将上演。
衡雍渡口的芦苇已白,公子遂的车驾碾过霜地,车轴发出“咯吱”声响。对岸,晋国正卿赵盾身着玄色朝服,腰间佩剑在晨霜中闪着寒芒。两人在黄河故道的土坛前相遇,身后各站着二十名甲士,矛尖上的红缨在风中猎猎作响。盟约竹简展开时,墨迹在霜气中凝成白雾:“晋鲁同恤王室,共讨不庭”——这看似尊王的誓词,实则是赵盾为巩固霸权的布局。坛下埋着的牺牲尚未冷透,公子遂便瞥见赵盾袖口露出的青铜腕甲——那是当年晋文公伐楚时的遗物。黄河在不远处咆哮,仿佛在嘲笑这场以“尊王”为名的权力交易。
三日后,公子遂的车驾转向东南,在暴地的榛莽间遇见雒戎的首领。这些身着兽皮的部族首领腰间悬着石斧,与公子遂车上的青铜礼器格格不入。盟约用朱砂写在鹿皮上,内容却出人意料:鲁国许以粮食布匹,换雒戎在伊洛之间牵制楚国。当公子遂将刻着“鲁侯之印”的玉符递给戎首时,忽听密林深处传来狼嚎——那是他昨日在衡雍结盟时,赵盾麾下谋士提及的“南蛮北狄交侵”之兆。暮色中,公子遂回望来路,暴地的土丘像一头蛰伏的巨兽,而他刚埋下的,不知是结盟的信物,还是祸乱的种子。
鲁国大夫公孙敖的逃亡成了这年冬天的奇闻。他本奉使吊唁周襄王,行至齐鲁边境却突然折返,家臣们只知他在途中收到一封莒国来信。当鲁僖公派人追查时,公孙敖已带着家财姬妾出了莒国城门。有人说他是因与嫡妻争权而逃,更多人私下议论:他在周襄王丧仪前逃亡,恰是避开了即将到来的诸侯混战。莒国都城的守卒记得,公孙敖入城那日,车驾上装着几口沉重的木箱,行至城门时,箱缝里不慎掉出一片玉简——上面刻着“关市之征,以佐王用”的字样,那是周室秘藏的税则,此刻却成了大夫逃亡的盘缠。
与此同时,当鲁国的田野被蝗群染成黑云时,宋国的内乱已达顶点。大夫司马因谏阻新君厚葬周襄王而被诛杀,鲜血溅在太庙的石阶上,惊飞了檐下筑巢的燕子。司城官署的属吏记得,司马临死前捧着一卷《汤誓》疾呼:“夏桀暴虐,汤武革命!”而司城逃奔鲁国时,车中载着宋国历年的关税账册——那些记录着“桑林之税”“陶丘之赋”的竹简,如今成了他叩开鲁国门扉的凭信。鲁国边境的关吏查验账册时,发现其中一页用朱砂圈着“郑商弦高犒师”的旧案,墨迹透过竹简,在背面洇出一个暗红的指印,像极了此刻宋国都城上空弥漫的血腥气。
这一年的冬雪来得格外早,覆盖了周襄王的陵墓,也覆盖了衡雍的盟坛、暴地的榛莽。当鲁僖公在太庙占卜来年吉凶时,龟甲上的裂纹竟分成三股:一股指向洛邑的新王,一股指向晋国的赵盾,最后一股,却蜿蜒着指向东南——那里,莒国的驿道上,公孙敖正对着莒子展开一卷泛黄的周室税则,而宋国的司马府中,血水流过竹简,将“关市之征”四个字染得通红。
话说回来,就在周襄王在位第三十三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同时也是鲁文公执政鲁国第八年春季的时候,料峭寒风仍裹挟着残冬的肃杀,晋国都城绛城却已呈现出一派忙碌景象。晋灵公端坐于巍峨的朝堂之上,目光扫过阶下群臣,心中盘算着新的战略布局。权衡再三后,他召来大夫解扬,下达了一项看似慷慨实则暗藏深意的命令——归还卫国匡、戚两地的田地,并将昔日公婿池划定的,从申地至虎牢境内的郑国疆域悉数奉还。
解扬领命后,即刻着手筹备归还事宜。一队队晋国士兵有条不紊地收拾行装,撤离匡、戚两地。卫国百姓听闻故土将还,起初满心疑虑,不知晋国此举是何用意。待看到晋国军队真的开始有序撤离,百姓们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路边,眼中既有对回归故土的期待,又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一些老人更是老泪纵横,口中念叨着终于能重回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与此同时,前往郑国归还疆域的队伍也踏上了行程。一路上,晋国使者手持文书,向沿途郑国百姓宣告晋国的决定。郑国百姓同样感到惊讶,对于晋国突如其来的“善意”,他们既惊喜又不安。在郑国朝堂上,君臣们围绕此事展开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晋国示好之举,可借此机会缓和两国关系;也有人担心晋国另有图谋,归还土地不过是权宜之计。
然而,就在各国还在揣测晋国意图之时,夏日的热浪尚未完全席卷大地,秦国便以雷霆之势打破了短暂的平静。秦国人对令狐之战的耻辱耿耿于怀,此番,他们精心谋划,决意攻打晋国,以报一箭之仇。
秦国大军在将领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晋国进发。士兵们身披战甲,手持兵器,士气高昂。沿途的百姓听闻秦军来袭,纷纷惊恐逃窜,原本宁静的村庄瞬间变得萧条冷落。晋国边境的守军得到消息后,立即严阵以待,可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双方军队在武城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战场上,金鼓之声震天动地,喊杀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秦军因复仇之心驱使,个个奋勇争先,如猛虎下山般扑向晋军阵地;晋军则凭借武城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箭矢如雨点般射向秦军。一时间,鲜血染红了武城的土地,尸体堆积如山。经过数日苦战,秦军凭借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战术,终于攻破了武城的防线,占领了这座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