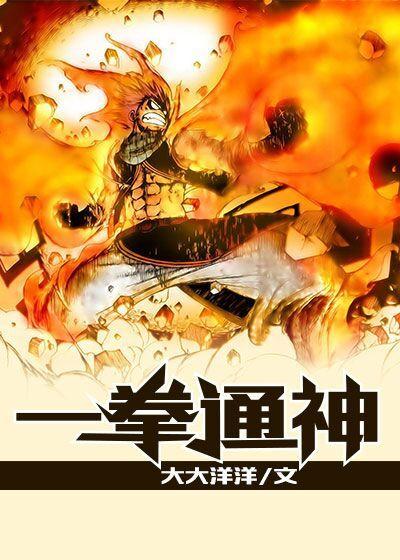趣书网>燕辞归人物关系图 > 第536节(第1页)
第536节(第1页)
&esp;&esp;我这几年浑是浑了些,但也不是烂到骨子里了,可能是年纪到了,十岁冒头能沉迷斗鸡斗蛐蛐,快二十了还是得有点人样。
&esp;&esp;朱姑娘认得安逸伯对吧?
&esp;&esp;他家那几个孙儿,小时候还是我的手下败将。
&esp;&esp;说这个不是想自吹自擂,就是想说,我多少有些基础,不是手不能挑肩不能扛,脑袋一热就去送死了。
&esp;&esp;真连刀枪都不会,我吵着要去,我家里也不敢让我去。”
&esp;&esp;听他这么说,朱绽平复许多。
&esp;&esp;也是。
&esp;&esp;喻诚安上头长辈多,他敢寻死、家里有的是办法阻拦。
&esp;&esp;既然没有拦,那就是赞同他改一改原先的纨绔脾气,走一走正经路子,哪怕这路子有风险。
&esp;&esp;喻诚安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我就是要离京了,嘴上讨个便宜,最后替自己争取一把。
&esp;&esp;刚才想到的,许是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定下,我真的再无机会了。
&esp;&esp;当然,我不是为了让你点头才选择从军,更不会因为你不点头就不好好操练、给战局添乱。
&esp;&esp;从军是为了自己,这一句不是骗你的。”
&esp;&esp;朱绽一时无言。
&esp;&esp;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上一次他们面对面时一般,只是局面调转过来了。
&esp;&esp;上一回,是她一席话堵得喻诚安说什么都恰当,而这一次哑口无言的是她。
&esp;&esp;明明有许多话语,却是无从说起。
&esp;&esp;好像说什么都不合适,都对不起这份坦率与赤忱。
&esp;&esp;是啊。
&esp;&esp;她是见过不少纨绔。
&esp;&esp;她的父亲朱骋就是纨绔中的“表率”。
&esp;&esp;可论心性,她能感觉到喻诚安与朱骋是截然不同的人。
&esp;&esp;不是烂到骨子里吗?
&esp;&esp;朱绽徐徐舒了口气,许是胸中郁气也散了许多,许是喻诚安这一走有可能永远都回不来……
&esp;&esp;她抬起头,直视着喻诚安的眼睛:“我母亲走了两年。”
&esp;&esp;喻诚安眉梢一抬,转了个弯才明白朱绽的意思。
&esp;&esp;“是,你还有一年孝期,”他恳切道,“那就先看一年?这一年里我在裕门要还像个样子,你到时就考虑考虑?”
&esp;&esp;朱绽呵地笑了笑,很轻也很快,笑容在脸上一闪而过,心情倒是越发舒展了些。
&esp;&esp;“等你从裕门回来,我把考虑的结果告诉你。”
&esp;&esp;喻诚安笑了,笑意久久不散,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esp;&esp;他知道朱绽其实并没有应允什么,但比起前次那样斩钉截铁的拒绝,还是进步良多。
&esp;&esp;正如他说的,他的改变出于本心而不是为了朱绽,得任何结果他都不会怨怼。
&esp;&esp;不过,若是这份改变能落在朱绽的眼中,让她不再将他视作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他当然也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