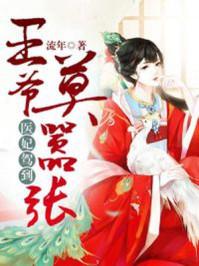趣书网>短篇鬼故事录 > 第283章 墨汁铺的人血朱砂墨(第6页)
第283章 墨汁铺的人血朱砂墨(第6页)
她看了眼身边的赵阳,少年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慌乱,眼神里多了些东西,像被血墨洗过的坚韧。他攥着那把刻着枣子的砍柴刀,脚步坚定地朝着官府的方向走去,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通往救赎的路。
只是他们都没注意,墨汁铺柜台的裂缝里,还残留着一滴没被清理的墨汁,那墨汁在晨光里慢慢蠕动,最后凝结成个小小的“灵”字,然后迅隐没在木纹里,仿佛从未存在过。
赵阳跪在墨汁铺的柜台前,用块粗布蘸着清水擦拭柜面上的墨渍。那些暗红的印记像是生了根,擦了三遍仍留着淡淡的痕,凑近了闻,还能嗅到松烟混着铁锈的腥气——和血朱砂墨的味道一模一样。
“别擦了。”林婉儿站在门口,月白色短褂已经浆洗得白,她手里提着个布包,里面是刚从官府取回来的账本,封皮上盖着朱红色的官印,“官府说王启年的罪证确凿,牵连出三个当年包庇他的官员,都判了流放。赵家村的枣园也归还给村民了。”
赵阳没抬头,粗布在柜面上划出沙沙的响:“我想把这铺子盘下来,卖正经的松烟墨。”他的手腕上缠着新的红绳,遮住了那圈洗不掉的暗红印记,“灵儿说过,她想看看不用血炼的墨是什么样的。”
林婉儿走到他身边,看着柜台裂缝里那点若隐若现的墨色——那是上次漏清理的“灵”字,如今竟长得和木纹融在了一起,像天然形成的纹路。“你确定要留下?”她的指尖划过那道纹路,触感冰凉,“这里死过太多人,怨气重。”
“我不怕。”赵阳终于停下手里的活,他的眼睛在晨光里亮得惊人,“李道长用魂镇了邪祟,灵儿也解脱了,这里该太平了。”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是那半块从王启年邪祟身上掉下来的血墨锭,墨锭里嵌着点布丝,是赵灵儿红棉袄上的,“我想把它埋在老枣树下,让它陪着枣树长。”
林婉儿没说话,只是从布包里拿出支毛笔——那是李承道留在后院的血墨笔,笔杆上的“赵德”三个字已经被她用砂纸磨掉,换成了新的刻痕:“承道”。“我要走了。”她把毛笔递给赵阳,“师父说这杆笔沾过他的魂,能镇住零星的邪祟。你留着用。”
赵阳接过笔,笔杆温润,像是有体温。他突然想起什么,从柜台底下拖出个木箱,里面是他这几日赶制的松烟墨,墨锭泛着乌润的光,上面刻着小小的枣花:“这些墨你带些走,路上用。”
林婉儿拿起一锭墨,墨香清冽,没有半点腥气。她的指尖在墨锭上轻轻摩挲,突然停住——墨锭的断面上,竟有个极淡的“灵”字,像是天然形成的。
“怎么了?”赵阳注意到她的异样。
“没什么。”林婉儿把墨锭放进袖袋,指尖却有些颤。她想起李承道最后那句话:“血墨可灭,人心难镇。”当时只当是感叹,现在才隐约明白,有些执念,根本不是死亡或解脱能斩断的。
两人沉默地收拾好东西,锁上墨汁铺的门。门环上的铜锈被赵阳擦得亮,阳光照在上面,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像极了李承道和赵德当年站在这里的模样。
走到巷口时,林婉儿突然回头:“对了,官府在王启年的卷宗里找到这个,是十年前赵德写给你的,一直被压着没送出去。”
信纸已经泛黄,赵德的字迹却依旧有力:“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叔公应该已经不在了。那血墨里的冤魂,其实不止灵儿一个,还有当年偷贡品枣被灭口的乡亲——王启年用他们的血炼墨,既镇邪祟,又灭罪证。我护不住他们,只能护你……”
赵阳的手指捏紧信纸,纸页边缘被攥得皱。他突然想起地窖里那些嵌着布料的碎墨,想起张屠户的媳妇抱着孩子的身影——原来王启年的罪,远比他们知道的更重。
“对了,”林婉儿的目光落在柜台的裂缝上,那里的“灵”字已经完全融入木纹,不细看根本现不了,“我在江南见到个老道士,他说李承道的师父曾留下句话:‘血墨成于人心,亦灭于人心,若有天墨魂复现,需以三代血亲之泪洗之。’”
赵阳的心猛地一跳,他看向后院的枣树,树上的红枣已经熟透,红得像血。风吹过枣叶,出“沙沙”的响,像有人在笑,又像有人在哭。
当晚,赵阳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十年前的墨铺,赵德正往墨缸里倒朱砂,李承道站在旁边画符,赵灵儿穿着红棉袄,举着颗青枣跑到他面前:“阳儿哥,这个给你,甜着呢。”
梦醒时,天刚蒙蒙亮。赵阳走到柜台前,现砚台里的墨锭上,竟凝着颗小小的露珠,露珠里映出个模糊的人影,梳着双丫髻,正对着他笑。
他拿起李承道留下的那杆笔,沾着露水在宣纸上写字,笔尖落下的瞬间,纸上竟自动浮现出一行字:“枣熟时节,魂归墨间。”
赵阳的手没有停,笔尖继续游走,写出的字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最后在纸的末尾,落下个清晰的“灵”字。
字刚写完,后院突然传来“咚”的一声,像是有颗熟枣掉在了地上。赵阳放下笔,往后院走去,月光下,老枣树下站着个小小的身影,手里拿着颗红枣,正对着他笑。
“阳儿哥,枣子熟了。”赵灵儿的声音清甜,像刚从梦里醒来,“你说过要喊我尝尝的。”
赵阳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枣,咬了一口,甜得腻,甜里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墨香。他知道,有些魂,根本舍不得离开;有些债,要用一辈子来还。
赵阳把那颗枣核埋进土里,就在老枣树的根旁。埋下去的瞬间,他仿佛听见泥土里传来细微的声响,像是种子破土的动静。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月光落在他手腕的红绳上,绳结处的暗红彻底褪去,露出干净的赤红,像极了赵灵儿红棉袄的颜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墨铺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往来的文人墨客都说,赵家墨铺的松烟墨里藏着灵气,写出来的字带着股鲜活的劲儿,尤其是那枚刻着枣花的墨锭,墨香里总缠着点清甜,像是初秋的枣子刚被晨露洗过。
入了冬,第一场雪落下来时,林婉儿寄来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在江南遇到了个老匠人,正在学古法制墨,还说那边的梅花墨极美,等开春了就寄一锭来。信的末尾画了个小小的枣子,旁边写着:“人心若净,墨自清明。”
赵阳把信折好,夹在那本浸过血墨的账本里。账本被他用松烟墨重新裱糊过,封面上写着“记”字,笔锋沉稳,再无当年的颤抖。他知道,这本账不仅记着王启年的罪,记着赵德的悔,记着李承道的赎,更记着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愧疚与原谅。
除夕夜,他独自一人在墨铺守岁。炉火噼啪作响,映得墙上的影子忽明忽暗。他研了一砚新墨,用李承道留下的那杆笔,在宣纸上写了副春联:“墨里洗冤魂,笔下生太平。”
写完放下笔,却见砚台里的墨汁中,浮着个小小的枣花影子,随墨汁轻轻晃动。窗外的雪地里,不知何时多了串小小的脚印,从后院的老枣树一直延伸到门口,脚印浅得像梦,却在雪地上留下淡淡的红,像极了赵灵儿红棉袄上的花纹。
赵阳笑了笑,起身去开门。门外的雪光里,仿佛站着个梳双丫髻的小姑娘,手里举着颗冻得通红的枣子,眼睛亮得像落满了星光。
“阳儿哥,新年好。”
他侧身让开,往炉子里添了块炭:“进来暖暖吧,我煮了枣茶。”
炉火映着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再也不会褪色的画。而柜台裂缝里的“灵”字,在火光中泛着温润的光,与木纹彻底融为一体,成了这墨铺最安静的秘密——就像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执念,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不扰人间,只伴岁月。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