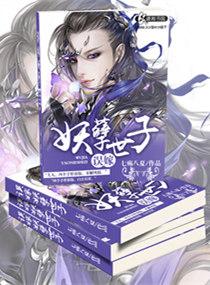趣书网>大唐:全能太子,李二直呼内行 > 第50章 皇帝怕的不是药是药怎么被人吃(第2页)
第50章 皇帝怕的不是药是药怎么被人吃(第2页)
药政可以推行,制度可以完善,但百姓记住的,是东宫的恩情,是太子的仁义。
李二默然良久,挥了挥手,示意孙思邈退下。
他命内侍取来《药政院日录》,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药政推行的点点滴滴。
他一页页翻看着,目光最终停留在了一页上,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协济医总数:四百一十七人。”
“他养了四百个嘴,全都替他说话。”李二叹息一声,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他终于明白,太子不仅仅是在推行药政,更是在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
这四百多名协济医,如同四百多个喇叭,日夜不停地在百姓耳边,诉说着东宫的功绩。
长孙无忌再次来到高履行府上,密室之中,气氛凝重。
“太子真要夺权?”长孙无忌开门见山,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
高履行摇了摇头,神情复杂:“他不要权,他要的是‘理’。百姓信他给的药,就是信他给的理。”
“理?”长孙无忌喃喃自语,仿佛在咀嚼着这个字眼。
他突然意识到,太子所图甚大,他不仅仅是想要获得权力,更是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重塑社会的秩序。
“可理一多,天子就成了摆设。”他抬起头,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高履行。
高履行沉默不语
如果百姓只相信“理”,而不相信皇权,那么皇帝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两人对视良久,最终达成了一致——必须制衡太子,维护皇权的稳定。
长孙无忌决定亲自出面,奏请皇帝,将药政院改隶尚书省,从而削弱东宫对药政的直接管辖权。
消息传到东宫,徐惠有些担忧地看着李承乾:“殿下,长孙大人此举,分明是针对我们。”
李承乾却不怒反笑,他拿起桌案上的《巡医三年录》,缓缓地递给徐惠。
“将这本《巡医三年录》提前呈递上去,记住,封面要题上这句话。”
徐惠接过《巡医三年录》,只见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药非臣所创,信非臣所求,然民有所需,臣不敢不应。
她瞬间明白了太子的用意,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报告,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份对百姓的承诺。
甘露殿内,李二正襟危坐,桌案上摆放着那本《巡医三年录》。
他一页页翻看着,目光最终停留在了一页手稿的影本上。
那是武媚娘改良药方的手稿,字迹娟秀,却充满了智慧和力量。
手稿旁边,还附着百姓的口述:“提灯娘娘走后,灯使来了,药更灵了。”
李二如遭雷击,瞬间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那夜送药的火种,早已被太子接过去,并且炼成了一种制度,一种深入人心的信仰。
次日早朝,百官肃立,气氛庄严肃穆。
长孙无忌刚要启奏药政院改隶之事,李承乾突然站了出来,朗声说道:“父皇,儿臣有一事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