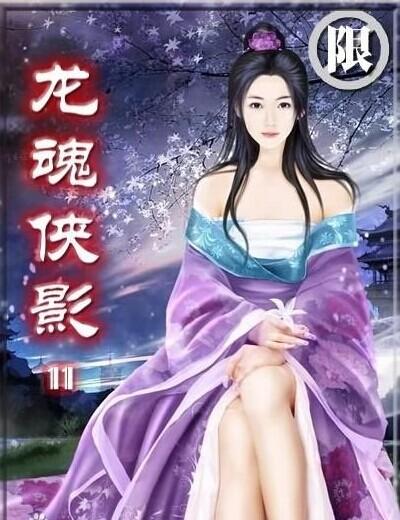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直播一战,法国人先傻了! > 第108章 诞生在法庭上的元首(第1页)
第108章 诞生在法庭上的元首(第1页)
天幕上的时间显示为:慕尼黑,1923年11月9日。
空气里弥漫着啤酒、汗水和一种病态的亢奋。
两千多人的队伍像一条蜿蜒躁动的巨蛇,挤满了狭窄的街道。
刺眼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上面写着“打倒十一月罪人!”的口号,墨迹未干,透着一种仓促的狂热。
队伍最前方,穿着那件标志性旧军大衣的阿道夫,脸色因为激动而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他身边,是一战传奇名将鲁登道夫。后者穿着笔挺的旧式将军服,胸前勋章累累,下巴高昂,步伐带着阅兵式的刻板,仿佛正率领大军走向凡尔登,而非一群乌合之众穿过慕尼黑的啤酒馆区。
“进军!向市中心进军!”阿道夫嘶吼着,手臂挥向歌剧院广场的方向。
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应,声浪撞击着街道两旁的玻璃窗。
然而,这支队伍混乱不堪。有人醉醺醺地挥舞着捡来的木棍,有人穿着不合体的冲锋队制服,更多的人只是被裹挟着前进,脸上混杂着茫然和一种被煽动起来的、廉价的愤怒。
他们经过了军营门口,卫兵警惕地注视着,黑洞洞的枪口在阴影里若隐若现。
队伍没有停下,阿道夫甚至没有朝那个方向多看一眼。
电话局?警察总局?这些控制城市命脉的关键节点,在他那充满瓦格纳式戏剧幻想的“进军”蓝图里,似乎被彻底遗忘了。
他深信,仅仅靠“人民”的声浪和身边这位帝国军神的光环,就足以让整座城市匍匐在脚下。
天幕之下,1914年6月27日的鲁登道夫少将,正看着天幕上那个1923年昂首阔步、置身于混乱人群中的“自己”,眉头越拧越紧。
这种组织度?这种战术安排?简首是儿戏!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仿佛看到精心设计的战役计划被一个莽撞的下士涂改得面目全非。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比东线冬天的风雪更冷。
歌剧院广场到了。迎接他们的不是欢呼的市民,而是一道沉默而坚固的人墙。
巴伐利亚邦警察穿着深色制服,头盔在惨淡的天光下闪着冷硬的金属光泽。刺刀出鞘,枪口平端。空气瞬间凝固,先前的狂热嘶吼像被掐断了喉咙。
“散开!最后一次警告!”警官的声音透过喇叭传来,像冰冷的铁块砸在人群头上。
队伍停住了,骚动起来。前排的人被后面的人推搡着,不由自主地向前涌去。
阿道夫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试图稳住阵脚。
鲁登道夫依旧高昂着头,似乎不屑于与这些地方警察对话。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僵持中——
“砰!”
一声突兀、尖锐的枪响,撕裂了紧绷的空气。
紧接着,如同点燃了火药桶,爆豆般的枪声从警察防线和队伍混乱的前排同时炸开!尖叫声、哭喊声、咒骂声瞬间淹没了一切!烟雾升腾,血腥味刺鼻。
混乱中,阿道夫感到一股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狠狠撞在他的左肩上。剧痛让他眼前一黑,身体像破麻袋一样向后摔倒。他听到了骨头错位的、令人牙酸的“咔吧”声,剧痛让他几乎晕厥。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他蜷缩着,用还能动弹的右手死死捂住脱臼的肩膀,不顾一切地翻滚、爬行,像一条受伤的野狗,利用混乱的人群和街边的障碍物作掩护,向广场边缘的黑暗小巷拼命逃窜。
身后,是密集的枪声、倒下的身影和鲁登道夫那笔挺军装消失在烟雾中的、凝固的惊愕。
---
天幕上的时间地点变化为慕尼黑法庭,1924年4月1日。
镁光灯刺眼地闪烁,快门声密集如雨。
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各国记者的镜头贪婪地对准被告席。
焦点人物只有一个:一身笔挺将军礼服、胸前挂满勋章、下巴依旧习惯性抬高的鲁登道夫。
至于那个穿着褪色军装、面色苍白但眼神异常明亮的落榜生阿道夫则无人顾及。
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天幕上以及天幕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位一战军神身上。
只见天幕上的鲁登道夫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法官阁下,我郑重声明,我从未参与任何所谓的‘政变’策划!”
他刻意停顿,目光扫过旁听席,仿佛在检阅自己的军队,“11月8日晚,我是作为普通听众参加啤酒馆的集会。是这位阿道夫先生,”
他伸手指向旁边的被告,语气带着明显的疏离和轻蔑,“用虚假的承诺和煽动性的言论,欺骗了我!他声称巴伐利亚政府高层和军队都己支持他,人民己经觉醒!我,作为一个爱国者,出于对德国命运的关切,才在那种混乱和误导的情况下,出现在队伍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