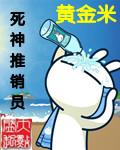趣书网>综视权臣 > 第64章 三法司(第1页)
第64章 三法司(第1页)
马车刚在窦府门前停稳,窦昭便听见车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车帘被掀开,露出窦世英略带憔悴却难掩关切的脸。
“昭儿,可算到了。”他伸手扶她下车,指尖触到她微凉的手,眉头不由蹙了蹙,“路上累着了吧?瞧这脸色白的,快进屋歇歇。”
窦昭被他扶着,鼻尖微微发酸。父亲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些,眼角的细纹也深了,分明是这两年操心得厉害。她轻声道:“爹,我没事,就是坐车久了有些乏。”
进了正厅,崔太夫人被丫鬟簇拥着上了主位,看着儿子对女儿嘘寒问暖的模样,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世英啊,你就是疼昭儿,也别挡着孩子歇脚。”
窦世英这才笑着让开,又吩咐下人备热水和点心。
窦昭刚坐下,就瞥见站在一旁的王映雪。她脸上没什么笑意,眼神扫过窦昭时,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冷淡,待看到窦世英对女儿那般关切,嘴角更是撇了撇,脸色沉得像要滴出水来。
“好了,人都到齐了,我有句话说。”王映雪忽然开口,打破了厅里的暖意,“明儿和马渊的婚事,既然官家都赐了婚,总不能拖太久。我看不如趁太夫人也在,挑个近点的日子,先把庚帖换了?”
窦明刚端起茶杯,闻言一口水差点喷出来,红着脸道:“娘!”
王映雪却不理她,只看着崔太夫人:“太夫人觉得呢?”
崔太夫人还没答话,王映雪又似笑非笑地补了句:“说起来这门婚事也是巧,原以为就是个寻常勋贵子弟,没成想竟是个要封伯的,咱们窦家这是走了大运了。”
这话听着像夸赞,却总带着点说不出的别扭。窦昭垂下眼,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王映雪向来不喜欢她,连带对窦明的婚事也这般急吼吼的,多半是想着赶紧把窦明嫁出去,好腾出手来安排别的事——比如她和济宁侯府的婚事。
“娘,你别说了。”窦明跺了跺脚,脸更红了,“我跟马渊就是见过几面,婚事是官家亲点的,我没什么想法。这次回京,就是想让祖母和姐姐见见他,别的别的再说吧。”
她说着,偷偷看了窦昭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求助。
窦昭心中了然,接口道:“妹妹说的是。刚回京,家里事多,婚事还是从长计议的好。先让马渊来府上走动走动,彼此熟悉了再说不迟。”
崔太夫人也点头:“昭儿说得对。明儿是咱们窦家的姑娘,婚事不能马虎。等歇几日,让马渊过来吃顿饭,我老婆子也瞧瞧人。”
王映雪见太夫人发了话,虽不情愿,也只能应了。
窦昭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越发清明。父亲性子软,王映雪又步步紧逼,还有虎视眈眈的济宁侯府她要退婚,怕是比想象中更难。
但她没有退路。
广平伯府的书房里,檀香袅袅。广平伯端坐在太师椅上,眉头微蹙,手里捏着一份刚从宫里递出来的抄报。
“今日朝堂上,出了件不小的事。”他抬眼看向对面的马渊,语气凝重,“福建总督蒋梅荪,你还记得吗?”
马渊点头。蒋梅荪是世袭的蒋国公,镇守福建多年,性子刚首,在军中颇有威望。
“台风袭了福建沿海,灾情不轻。”广平伯将抄报推给他,“这蒋梅荪,竟没等朝廷旨意,首接开仓放粮了。”
马渊拿起抄报快速扫过,指尖在“擅开官仓”西个字上顿了顿。
“说来也巧,”广平伯叹了口气,“前阵子江南叛乱,朝廷调福建黑甲军支援平安大营,蒋梅荪以‘沿海防备要紧,抵御海贼’为由,迟迟没动兵。朝中本就对他有意见,如今他又擅作主张,正好给了御史们由头。这会子,弹劾他的折子怕是能堆成山了,满朝上下,没几个肯为他说话的。”
马渊放下抄报,沉吟道:“开仓放粮救民,本心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没等旨意,坏了规矩。”
广平伯挑眉:“哦?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做?”
“先稳。”马渊道,“灾情刚发,百姓虽慌,却还没到绝境。此时不宜动官仓,该先动员地方士绅富户,募集民间粮草。”
他顿了顿,语气平静却透着条理:“募集来的粮食,不必精挑细选。一份粗粮混上三分糠麸做成馒头,煮出来的粥清得能照见人影,难以下咽才好。”
广平伯有些诧异:“这般难以下咽,如何救济灾民?”
“正因难咽,才是真救济。”马渊解释道,“寻常百姓但凡家里还有口吃的,都不会来领这掺了糠的馒头,稀粥。只有真正断了粮的灾民,才会为了活命咽下去。如此一来,粮食能精准到最需要的人手里,也能撑得更久。”
他看向广平伯,目光清亮:“等这掺糠的馒头,稀粥撑到朝廷旨意下来,那时再开官仓放精粮,既合了规矩,又能让灾民感念朝廷恩德。一来二去,时间就抢出来了,还不会落人口实。”
广平伯抚着胡须,越听越点头。这法子看似苛刻,实则是把粮食用到了刀刃上,既避开了“擅动官仓”的忌讳,又能最大化救济灾民,实在是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