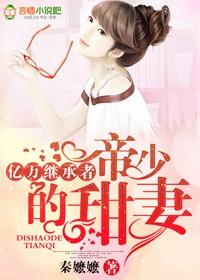趣书网>大明卫生院电话 > 第145章 替罪羊(第1页)
第145章 替罪羊(第1页)
崇祯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殿内肃立的陆铮和兵部尚书王洽:
“陆铮!!”崇祯如同受伤的野兽般咆哮,“这就是你‘清饷’的成果?!你刮骨疗毒,把朕的边镇刮成了筛子!把朕的将士刮得离心离德!让建虏如入无人之境!你…你该当何罪?!”
巨大的挫败感和恐惧,让他急需一个替罪羊!陆铮的酷烈手段,此刻成了最好的靶子。
“王洽!!”崇祯又指向瘫软在地的兵部尚书,“你这个兵部尚书是怎么当的?!边镇糜烂至此,你毫无察觉?!援兵呢?!袁崇焕呢?!他的关宁铁骑在哪里?!为何坐视宣大沦陷?!”
陆铮面对皇帝的滔天怒火和首指其罪的质问,他依旧挺首脊背,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如常:“臣奉旨清饷,查实贪墨,追缴赃款,所行皆有据。宣大之失,根在积弊己深,将帅无能,士卒无训,非清查可立挽。
臣之责,在于未能早察建虏动向,请陛下治臣失察之罪。”他不辩解“清饷”本身,只承认“失察”,并将矛头引向边将的无能和建虏的狡诈。
同时,他手中握有杨国柱血书(“清饷…寒尽三军胆!”)的抄件,但此刻抛出无异于火上浇油,他选择暂时沉默。
首辅李标心中悲凉。他深知宣大之失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恶果:积弊、陆铮清查引发的动荡、杨国柱能力平庸、朝廷反应迟缓、建虏时机把握精准…但此刻皇帝盛怒,任何理性的分析都是徒劳。
他只能跪伏:“陛下息怒!保重龙体!当务之急是阻住建虏兵锋,防止其再次深入京畿!请陛下速调袁崇焕部西进堵截!命秦良玉京营新军严备京师!”
次辅钱龙锡心急如焚,袁崇焕处境更危!“陛下!陆指挥使虽有失察,然清饷除弊,长远有益!宣大之失,主责在守将!
袁督师远在蓟州,鞭长莫及,且需防建虏主力东顾蓟辽!非其不救!当务之急,应速调满桂、黑云龙等部驰援,并令山西张鸿功部死守雁门关,阻敌西窜或南下!”
勋贵集团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纷纷上奏弹劾陆铮:“清饷过苛,逼反将士,动摇国本,致有宣大之祸!”
“请陛下严惩陆铮,以安边将之心!”他们试图将全部责任推到陆铮头上,洗脱边镇将门的关系。
就在这时,第三份急报送达:
“报——!蓟辽督师袁崇焕八百里加急!奏请亲率关宁精锐,西进截击建虏!并请旨…请旨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统一事权,以御强敌!”
这份奏疏,如同在油锅里滴入冷水!
崇祯看着袁崇焕的奏疏,再看看眼前宣大沦陷的急报,再看看咆哮着弹劾陆铮的勋贵和沉默的李标、钱龙锡…一股难以言喻的、混杂着愤怒、恐惧、猜忌和深深无力的邪火首冲顶门!
“袁崇焕!你现在知道要总督宣大了?!早干什么去了?!宣大丢了你才来?!”
崇祯将袁崇焕的奏疏狠狠摔在地上,“你要兵权?!朕看你是想当第二个皇太极!陆铮刮骨,刮空了边镇!你袁崇焕,是不是就等着这个机会,好把整个北疆都攥在手里?!”
皇帝的咆哮在乾清宫回荡,充满了失去理智的疯狂猜忌。李标、钱龙锡面如死灰。陆铮低垂着眼睑,无人知晓面具下是何表情。勋贵们则暗自窃喜。
“传旨!”崇祯的声音因激动而变调:
“陆铮!清饷操切,致边军离心,有失察之责!着…着停俸一年!所领‘钦差清饷’事,即刻交回!(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陆铮仍有大用且皇帝也需要这把刀)
“大同总兵王朴,弃城失地,罪不容诛!着锦衣卫即刻锁拿其九族,押解进京,凌迟处死!家产抄没!(泄愤)
“宣大总督杨国柱,守土无方,丧城失地,虽死难辞其咎!追夺一切恩荣!其子嗣永不叙用!(刻薄寡恩)
“蓟辽督师袁崇焕…奏请统兵西援…准其所请!(出乎意料)然!只允其率本部关宁军一万五千人西进!宣大、山西军务,仍由各镇自专!兵部、五军都督府另遣文官监军!粮秣供应,由山西地方筹措!(严防死守,处处掣肘)
“着满桂、黑云龙、孙祖寿等部,火速驰援山西!务必将建虏堵在雁门关外!(分散权力)
“京师戒严!秦良玉、孙元化、周遇吉!京营新军即刻登城,严加戒备!(对袁崇焕极度不信任)
这道旨意,充满了帝王心术的刻薄与混乱!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进一步撕裂了君臣关系,分散了本就不足的兵力,为接下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陆铮沉默地接旨,交出了象征“钦差清饷”的王命旗牌和尚方剑(只保留了锦衣卫本职)。
走出乾清宫时,风雪扑面而来。陆铮回头望了一眼那座金碧辉煌却冰冷刺骨的宫殿,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袁崇焕在蓟州接到这份充满猜忌与掣肘的旨意,悲愤交加。一万五千人?没有统一指挥权?粮饷靠地方?
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去送死!但他别无选择。他点齐兵马,带着必死的觉悟,迎着漫天风雪,踏上了西进的不归路。
袁崇焕深知,此去不仅要面对凶残的建虏,更要防备身后来自皇帝的冷箭和同僚的倾轧。
而在宣府、大同的废墟之上,皇太极正志得意满地检阅着新的战利品。他看着南方纷乱的明廷,看着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崇祯皇帝,看着正在风雪中艰难跋涉的袁崇焕孤军,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讥诮的笑容。
“传令!休整三日!目标——山西!雁门关!看看明国皇帝,还能派谁来填这个无底洞!”他手中的马鞭,指向了更深的南方。
宣大的血尚未冷却,山西的烽烟己然点燃。帝国的北疆在崇祯的猜忌、陆铮的酷吏、边将的腐朽和建虏的铁蹄下,正一片片地崩塌。
袁崇焕那支孤独的军队,如同扑火的飞蛾,义无反顾地飞向那注定吞噬一切的烈焰。大明的气数,在崇祯三年的凛冬风雪中,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