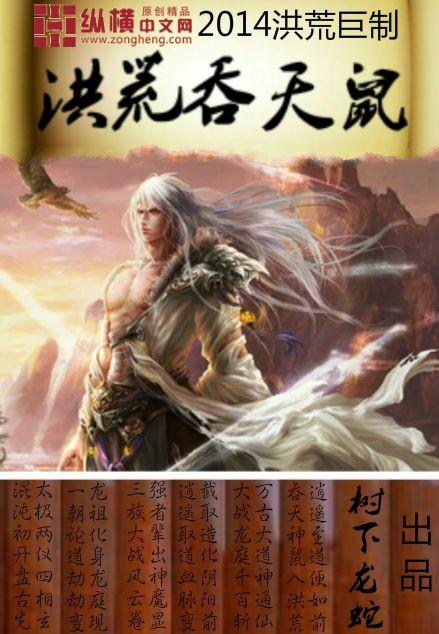趣书网>重生七零 木十一 > 第56章 败露(第1页)
第56章 败露(第1页)
茶馆二楼的隔间,光线昏黄,闷得人喘不过气。
狗日的薄木板,把耳朵硌得生疼。
陆骁全当没这回事,身子弓成一张拉满的弓,连呼吸都掐断了。
隔壁,王科长那破锣嗓子还在嗡嗡作响。
“建军老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冷库的采购权,往后可全攥你手里。”
陈建军的嗓子眼儿又干又哑,飘出来的字儿都带着一股烧糊的味儿。
“王哥,那……那批货,真能成?”
王科长喉咙里滚出一阵黏糊糊的笑声。
“呵,有啥成不成的?”
“南关黑市跛脚刘的货,便宜就是硬道理!”
“你就照我说的,把那批跟烂泥没差的水泥,还有那细得能拿来剔牙的钢筋换进去,天王老子来了也瞧不出半点毛病。”
“等工程款一到手,信封里这点钱票,就是个开胃小菜。”
“真正的大头,咱哥俩,对半分!”
这话一字一句,都往陆骁后心里钻,他浑身的皮肉瞬间绷紧,一层白毛汗从脖子根炸到脚后跟。
墙那边,传来一声响亮的吞咽,还有骤然粗重了好几倍的喘息。
……
夜沉得跟墨似的,院里黑黢黢的。
陈家老宅,陈秀英的卧房里,只有一豆油灯的火苗在跳。
陆骁垂着手站在炕边,嗓子压得极低,把偷听来的那些腌臜事,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
跛脚刘。
烂泥水泥。
剔牙钢筋。
对半分。
每吐出一个词,这屋里的空气就更冷一分,死寂得吓人。
话倒干净了,陆骁就立刻闭上嘴,眼皮子垂下去,不敢瞅老太太的脸。
奇怪的是,陈秀英听完,脸上千沟万壑的褶子竟没动一下,平静得过分。
可她那双浑浊的老眼,在昏黄的灯火下,却透出一股瘆人的亮光。
半晌,她嘴皮子慢慢咧开,一个冷冰冰的弧度。
手里的拐杖,笃,笃,笃,一下下敲着地面。
声儿不大,却敲得人心尖儿跟着一抽一抽。